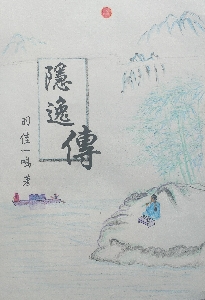在全国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口号声中,我们家的情况可是越来越不好了,这一点连不懂事的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感觉到了。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爸爸的工资是55元,妈妈的工资是45元,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刚好一百元。这个工资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当时青年工人夫妇的工资标准是,学徒第一年13元,第二年15元,第三年18元,第四年27元,第五年32元。32元是二级工的工资,但到了这一级,在文革期间工资就不再往上涨了。而我的爸爸妈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一百元,到了文革结束时,两人的工资还是一百元,整整十年期间,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增加过。
不错,十年文革工资没有涨,物价也没有涨。当然严格来说,物价还是有上涨,不过只是一部分物价上涨,对于城市居民凭票购买的东西,是一点也没有涨。比如买米要粮票,凭粮票到粮店里购买大米一斤是一毛四分钱,没有粮票到市场上去购买是市场价,最贵一斤达到四毛钱以上,差别还是不小。
文革十年,正是我成长发育的时候,夸张一点说,我们这个家庭所需要的饭量几乎每天都在增长。
所以我听得最多的是父母关于钱不够用的抱怨:“以前一丈布可以给两个孩子各做一件衣服,现在做两件都不够,你让我怎么办?”那时候物品短缺,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从平时生活的必需品,例如大米,面粉,食油,煤球,布匹,棉花,豆腐,肉等,到过年过节的非必需品,例如香烟,酒,糖等。别人家是票不够用,我们家是连这些票都用不完,因为没有钱去买,作废了可惜,只好作个人情送人。
妈妈为了用这一百元钱养活全家四口人,每天都记生活支出流水帐,每用一分钱,都记在帐上,不敢乱花一分钱。然而只节流,不开源,又有什么用?总不能让我们停止生长啊。所以只能以保证大家有饭吃为第一需要。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穿过新的衣服,后来大了,奶奶老了,没有人做了,便穿胶鞋,一双胶鞋穿三季,夏天放假不上学就打赤脚。冬天脚冻得实在受不了了,爸爸妈妈会挤出几毛钱来买一双毛草鞋给我。那是一种用芦花编织的草鞋,形状像棉鞋一样,鞋里塞些破旧棉花,比穿单薄的球鞋暖和多了。只是有一样不好,不能进水,也不能多行走,否则,一个冬天没有过完,鞋底就烂了。我记得直到1975年我上高二的时候,才第一次穿过一双新的胶底棉鞋。
我总是吃不饱。每天吃饭时是不允许自己盛饭的,爸爸统一替我们全家四口人盛饭,每人两小碗,刚刚好盛完预先煮的饭,如果让我自由发挥,就有可能最后盛的人吃不到第二碗饭了。吃菜也不允许自己夹,必须由爸爸妈妈用筷子一一分给我们,尤其是碰上难得吃一次肉,爸爸几乎在切生肉时就要计算好每人可以摊到几块,然后决定每块肉切的大小。
我们的口粮由政府统一规定,成年人每月定量是14公斤,小学生是12公斤,中学生因为正在长身体,每月定量16公斤。这些口粮,可以凭购粮证到指定的粮店里去购买。如果这个月没有买完,可以领粮票。如果不够吃,就要自己到市场上去买黑市粮。由于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吃肉,烧菜的食油也很少。食油不论大人小孩,都是每月每人零点二公斤。所以我们家额定口粮根本不够吃,每月都必须花许多钱去购买黑市大米,才能勉强维持全家半饱的状态。
市场上也有黑市食油,但是一般城市平民不怎么买,都是去买点肥猪肉来熬油,或者专门去买猪板油回家熬猪油,油渣还可以做菜。所以那时候,如果万一让我们去买猪肉,爸爸妈妈一定会在我们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一定要买肥肉!”
那时候老百姓也不都是像我家这么穷,比如说,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只生一个孩子,同样的工资就能生活得比较富裕。
但是,我们家的情况还远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当时学校的学费虽然不贵,每学期只需要几块钱,而且贫穷人家还可以申请减免。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标准是家庭人均工资在七元以下。我们家四口人,有一百元的工资,所以达不到减免标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学费都是每个月交一块钱,交完了差不多就放假了。虽然一个月才交一块钱,但因为我家有两个人上学,对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我不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十几岁以后,就经常去河道里钓鱼摸虾,抓田鸡,挖野菜,来充实和补充家庭食物的不足,,品尝过以番薯当饭,和将番薯掺在饭里充饥的滋味。
看看现在电视上整天播放怎样让孩子增加食欲的广告,我也常为自己的孩子吃饭不香而大伤脑筋,再想想我们小时候吃不饱的情形,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