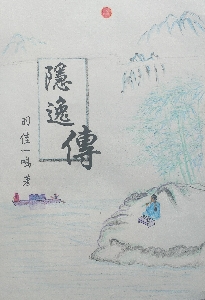从军用机械厂出来后,易副局长又连夜制订抓捕方案,全力以赴追捕三只手余谈。
但是,追捕又谈何容易?
从黄昏爆炸到午夜,几乎耽误了近6个小时才把各大交通要道设卡,要跑也早跑了。苟洱沉思着,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幕后策划人。可幕后人这么周密部署,也一定是经过了缜密测算的。想来想去,苟洱觉得这事一定有漏洞,但她一时摸不清楚漏洞的方向在哪。
“百密一疏!百密一疏!!”苟洱拿着水笔,不自觉地放进了嘴里咬着,舌头舔到了水笔尖,这时她才嗅到了难闻的酒精味,她猛然拍了拍脑袋:“那个血站和所谓的液化气分装车间还有那个平房没完!昨天虽然乱,但人多,总有几个有心人,也总会有人看到过什么,因为事情只要是有人做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苟洱又往军用机械厂的门卫跑。
已过了凌晨12点,值班的人已换成了一个六零后。这是一个兼了两份工的中年男人,略显老相,他选择当夜班是直奔睡觉来的,苟洱的到来令他不悦,但他也没有消极抵抗,只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凌晨5点多的时候,他去围墙边的厕所大便,正好看到有人从围墙上跳了下去,他没看清模样,那人蹲在墙上,他看到的是背个影,听到他呵斥了一声背影跳了下去。末了,他嘟哝着:“我每天都只当晚班,才500块一个月,我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吧?”
苟洱耸了耸肩膀,又问:“你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有楼梯吗?”
“什么楼梯?”
苟洱明白了。看来楼梯那会没有进来,应该在墙外,那人本想进来后再搬楼梯的,但来了人就吓跑了,昨天下午时却正好相反,是已经顺梯子下来踩完点,或者在作案了,没想到自己去了那,本来要把活做完再顺梯子跑出去的,哪知又来不及撤梯子。想到梯子,苟洱心里惊然地想道:如果爆炸成功,里面在作案的人一定会趁着慌乱而溜掉,既然三只手问好了没有,说明那个时候一定有人在里面,但三只手的弟弟已经死了,会是谁在和他打配合?这个人穷凶极恶,如果不尽快抓捕,后果只会很严重。
因为心里特别焦急,苟洱走路也快乐起来,等保卫和她一块赶到厕所围墙下的时候,她发现昨天的梯子已经不翼而飞了。
苟洱捶胸顿足了,当时如果自己不去现场,就守着这梯子,她一定能把凶手当场抓住!苟洱又问保卫:“你和厂里的‘三毛三’熟不熟?”
保卫说:“我才来几个月,哪里熟?另外那个保卫和他熟,他在这里做了好多年了,是秦总喊来的。听说原来安排了好几个,工资低了,没人来,卖厂那会,好像安排了一个工人,那人不肯来,厂里好像把他给告了,后来就更没人来了。我原来也不想来的,因为说只上晚班,在这里睡着就可以了,半夜查一次岗,其他不作要求,我也就答应了。”
“你们有进出登记本吗?”
“有啊,但是一般不登记,麻烦 ,厂里都破成这个样子了,好钢废铁谁不找机会带出去?你怎么记?查到了又怎样?你为了500块工资去和工人打架?他们气性大得很,和毛头小伙子一样,搞不好从口袋里掏出一坨废铁往你脑袋上一拍,那就泄了!”保卫装作被打一样往后一倒,苟洱心里觉得好笑,但她极力忍着。
“既然没有证据,秦艾艾凭什么在会上说厂里的保卫被‘三毛三’行贿?她一定是想让人知道货是从外面运进来的,她想让保卫承担责任,玩忽职守,或者徇私受贿,为她自己开拓。说不定幕后人就是她!”苟洱越想越觉得秦艾艾就是幕后黑手。
这次,苟洱毫无理智地推断,因为她一刻也不允许自己停留,她准备加大力度监视秦艾艾,可自己没有一官半职,要安排人手得层层报批,等安排得来,人都跑了,说不定中途就泄了密,她这会又想起当官的好来,想起当官的,她忍不住想起蒋局长,市委书记,罗书记就是罗佰义的父亲呢,他会亲自关注这个案子的吧?对了,不知佰义中了枪后怎么样了?苟洱听到他倒了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看他,可这些连环的案子,应接不暇,真是给忘了。她琢磨着是先找局里安排人手监视秦艾艾还是在血站及军用机械厂埋伏暗哨?自己还得进行一轮艰苦卓绝地深入调访,但不管怎么说,都要请示和汇报,这是雷打不动的。
苟洱把“进出登记簿”放进公文包的时候,保卫惊叫了一声:“蜈蚣!”
苟洱被蜈蚣咬过一次,心有余悸,吓得也惊叫起来:“哪里?”
保卫指了指小靠椅旁边的墙角,“喏,钻到屋角那个洞里去了。”
蜈蚣,为什么和自己如影随形?又是蜈蚣,无孔不入,怎么蜈蚣也盯上了自己?难道这和三只手有关系吗?苟洱反复琢磨着。
她又问:“你们这经常有蜈蚣出入吗?”
“哦我在这里值班看到过两次。”
“你不怕?”
“怕?当然怕!你们公安不怕?”
苟洱不好意思说不怕,“我是女的,女的就怕虫虫之类的东西。但坏蛋我不怕。”
“今天没熏药,要是熏了药,蜈蚣不会来。”
苟洱走了出来,她不想当着保卫的面给领导打电话汇报和请示工作,等到她走到厂门口的大灯下把手机拿出来滑开屏幕,看到了有7个未接电话,吓了一跳。两个号码,一个是办公室的,一个是易副的。
她连忙先拨易副的电话,但电话一通易副就说话了:“苟洱呀,你怎么不接电话,我都急起来了,怕你出了什么事!”
“你喜欢我出事呀?”
“你再皮,我撕烂你的嘴。你手好点了吗?”
“什么手?”
“你翻墙不是把手翻伤了吗?”
“哦,小事一桩,我都没理它。你打我电话就是讲这个?浪费时间和话费呀!”
“知道就好。”易副局长清了清嗓子,“你明天可能要去一趟贵州噢。”
“为什么?”苟洱惊暗想,难道是罗佰义在贵州医院治疗?她总是第一个念头就想起罗佰义来,虽然她知道这些和他并没关系。
“什么罗佰义?他还在边境执行任务,这里没他事。你怎么想起他来了?你想当小三?人家可没离婚噢!”
“局长!都什么时候了,您老人家欺负人也不是这样欺负的吧?”苟洱急得要扯人衣服了,可她忽然想到自己是在打电话,扯不上易副局长的衣服角的。
“嗯嗯,说正经事啊,刘生铁,就是刘驼子啊,他的大儿子刘大娃在贵州越狱逃跑了,贵州那边,昨天,就是晚上我们开现场会的时候传过来的消息,他应该是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估计他是听到刘驼子死了,他来复仇的。”
“他都逃过来了,我还去贵州干什么?他人又不在贵州。”苟洱反驳道。
“傻的呀,我又不是要你去抓他,我只是要你去摸一摸他在贵州的案底,抓他的事,我这边另外安排了人了,你不用管啦。”
“我不去。”
“什么?你不去?你……”易副局长气得打了一个嗝,肚子里装了一肚子的烂茶叶都倒了出来了。
“我要留下来抓‘三只手’。他是破这个爆炸案的关键!我觉得这个厂里就是迷魂阵,您不觉得蹊跷吗?”
“就是因为蹊跷,才派你去的。本来,这事是让你队长给你派活的,但他没空,你直接负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你不觉得,我们一直都忽视了刘驼子他的两个儿子吗?自从他死了以来,这边发生的事几乎都和他有关。”
“阴魂不散。我想再找厂里的其他工友聊聊,看看有什么新线索。”
“你可以休息了,只限今晚啊。暗访的事,我也布置了,你也不用操心。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刘驼子的两个儿子,他的小儿子还不知在哪里,你想想,爆炸呀,这么大的动作都能做出来,下一步,他还会做什么?我想,公检法,他都敢炸的。这边已经是天罗地网,他只要钻进来,我就让他有来无回!”易副局长斩钉截铁地发了狠话。
苟洱分明听到了易副局长上下牙齿互相咬合的声音。
赶到贵州时已经下午四点半了。
罗坪派出所的所长接待了苟洱。
他搬出了所有的卷宗让苟洱查。苟洱从尾到头地翻,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翻完了。
原来刘大娃是去年过年前后作的案,还不止一起,但入狱却是今年4月份。作案基本就围绕着陈花花老家和牛贩子居住的村庄为原点展开的。
苟洱嗫嚅了一句:“真没出息,也不跑远一点,全吃窝边草,有意思吗?”
罗坪派出所所长问:“谁没出息?”
苟洱怕他误会,忙摇手以示不是针对他的,所长却满腹狐疑,又不好多问。
看了一组刘大娃剃了光头入狱的照片,苟洱想起了刘驼子和陈花花。刘大娃的五官很像他父母,脸继承了母亲的圆盘脸型,耳朵眼睛额头极像刘驼子,看了他的相,可以完全不必怀疑陈花花借种的可能。
“有刘细娃的照片吗?”苟洱问。
“谁?”所长问。
“刘大娃的弟弟,刘细娃。”
所长说:“刘大娃至今没有正式名字,他弟弟肯定也没有名字了。刘大娃连身份证都没有,严格地讲,法律都管不着他,但他实在作恶多端,当地村民强烈要求惩处他,不管不行啊!村里人嚷着喊着要给他判死刑,我们判不了他,村民去检察院闹,说他是‘黑人’,就是马上毙了他也没关系,这事闹得有点厉害。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叫他‘刘大娃’。
苟洱高兴地说:“正好,我们那边也是这么叫的。”
所长也乐了,“哈哈,那“刘大娃”的弟弟就刘小娃了!”
“哦,那可不是,我们叫他刘细娃,不叫小娃。”所长饶有兴致地看着苟洱,苟洱接着说,“为什么村民们会这样义愤填膺呢?”
“这你问对了,我们这边的村民们觉得偷人没关系,但偷了他们的牛,那就是死罪。”所长解释。
苟洱点点头,心里想:刘大娃为什么跑到他妈老巢去偷呢?莫非他很熟悉这里?他不知道自己偷牛是村里十恶不赦的罪吗?当初,刘大娃被判了两年,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已经有一年了,再熬个秋天就可出来了,干嘛这么火急火燎的越狱?他越狱只是为了搞爆炸?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西藏人杀的,他只要杀西藏人就好了,干嘛杀其他无关的人?何况,他舅舅陈军军也是协犯,他们俩很可能都判极刑,他有必要做“雨后送伞——多此一举”的蠢事吗?
苟洱又翻了翻卷宗,看到审讯时,他说自己是一个人作的案,说着说着,又变成了两个人,还有人为他放哨,再问两遍,他又说没有,死扛着没有。讲到卖牛时,他又说不清楚卖给了哪里的牛贩子。
罗坪派出所所长说:“我们按他说的地方和特征去找那买牛的人,根本没那人,卖活牛和死牛的集市也没人,包括做手工皮包皮带皮鞋的店都跑了,没有人卖牛给他们。他偷的牛被送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都没定案哩!我知道他在耍滑。但好歹把他抓到了,应该判重些,只是以前的证据都没处找。”
“你们不是当场抓到他偷牛的吗?怎么不见了牛呢?”苟洱很费解地问。
“按理是这样,但他是特殊。我们是根据村民的报案去抓的他的,因为村里丢了好几头牛了,我们接到偷牛的案子有好几起,并不仅限于三头村一个点,村民见我们没破出案,就自己蹲点。他们守了三天四晚,在天光的时候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地进村到处看牛棚,但就是不下手。后来在天已蒙蒙亮的时候,那人靠近了牛棚,去摸睡起的牛背,村民们一窝蜂跑了上去,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扭送到所里来了。”
“脏都没分你们就抓了?”
“村民们说那就是偷牛,如果不惩罚,下次抓到直接打死,不会再送来了的。他们可是做得出的哟。跑马村就打死了一个偷牛的。现在都没有定案。”
“那刘大娃自己也承认?”
“承认!承认呀!当然承认,还很痛快,但要是问他同伙,他就不承认了。一副打死也不承认的架势。”
“他还是很恪守行规的,算个江湖黑客。”苟洱戏言。
“我也这么认为。他还有个弟弟,现在不知在哪里行窃。”
“所长,您怎么知道他在行窃?”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起的事吗?”
苟洱被所长说得不好意思了,这些天又没好好睡觉,脑子严重不够用。她准备去洗个澡,休息一下,晚再上跑一趟刘大娃越狱的监狱。
因为兄弟单位的关系,所长安排在新天地广场东边那牛肉店吃个便餐,宾馆也安排在那楼上。苟洱喜欢自由一些,不想被拘束了,但所长坚持,他说要去麦古塘监狱,必须经过那个新天地广场。苟洱见他们如此盛情也就不再推辞了。
沐浴完,她换上了便服,把头发用小的鸭嘴夹给夹住了,显得俏皮和可爱,她甩了甩头发,站在镜子前,又扭动了一下腰,不觉自己也风情万种起来,胸脯一起一伏的,一种生理性的冲动徐徐上升,她意识到,自己此时的寂寞可以舒广袖了。可自己就是跨不出那一步,尽管钱巍对自己处处迎合,百般迁就,不知道怎么的,心里总觉得有什么放不下,即使万般渴望,一到关键时候,罗佰义那张英武帅气的脸就浮现出来。苟洱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她忽然看到镜子里自己身后站了一个人,是罗佰义!他低下头,轻轻把下巴放在自己肩膀上,那眩晕的气息从鼻子里钻进了心房,她忍不住意乱情迷起来,苟洱准备转身去拥吻,等她再看镜子时,刚刚那个罗佰义已经不见了,她缓过神来,重重叹了一口气。这样的幻觉自她掉进罗佰义的情坑后就不断复出,不是在梦里就是在沐浴后,尤其是在出差回屋后。
幻觉完的苟洱失魂落魄地坐在床头,看着窗外的广场在夕阳中热闹起来。这时,钱巍的电话进来了:“亲爱的,你在干吗呢?”
“你是钱巍吗?”
“当然是呀,怎么了?”
“你怎么堕落成现在网络肥皂剧里痞子一样的人了?”
“有吗?哈哈”钱巍被抢白了一顿并没有不高兴,反而大笑,“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消息够灵通的了。回来干吗?你知道我不会结婚的,也不会和你结婚。”
“哎,不是扯这个,我跟你说吧,妙儿的儿子快不行了,打罗佰义电话打不通,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看看谷妙儿,好不好?”
“你的老相好,喊我去看干嘛?”
“你说话直接,我喜欢,但不要说过头了,说得难听,我就不爱了。”
“不爱还来找我说话干嘛?”
“你一个人在外办差,一定要把枪带好,上好膛,路上小心点,让那边的兄弟多担待一点。”
“你真的啰嗦得要死了,我爷爷恐怕都没你那么啰嗦。”
“要你真是我的老婆,我说什么都不让你干这个危险的活。”
“我愿意!我喜欢!”
“别跟我谈理想,谈主义,我不爱听,我只想和你谈爱。”
“我呸!你要今天不发情,没准我就和你谈谈爱了。”
“我发情?你发情了吧?你不是这几天排卵期吗?”
苟洱惊讶了:“你怎么知道我排卵期?”
“会加减法的人都知道呀。”
“说!不说我把你脑袋拧下来!”苟洱愤怒道,她对钱巍能明察秋毫的窥视能力表示震惊,这种羞于启齿的闺房秘事怎么能让他这样的人知道呢?
钱巍说:“其实,你也可以用我的这个办法推算出我的排精期,挺准。”
“你什么时候有个正形呢?”
钱巍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就是上次,次我们去牛扒店吃饭,你上了一趟厕所,后来你走了,我买了单,跑了一趟厕所,跑错了,我到女厕所去了,看到蹲位有你的留的下痕迹。”
“喂,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留下的?”
“旁边那个蹲位没有纸巾,也没有那玩意呀!”
“那你怎么就不判断我冲走了呢?”
“纸巾可以冲走,但那玩意你不会冲走,你这个人认死理,认准的永远不改的。人我就不说了,你用卫生纸、卫生巾、牙膏、毛巾、牙刷包括你所有的日用品,你只用一个品牌,一贯的啦。”
“那你怎么断定不是其他人也刚好用我这个牌子?”
“哈哈,你那天心情烦躁,四周都不看,我可看得清清楚楚,除了包厢里有一桌,大厅就我们俩,还有别人吗?再说,你去洗手间的时候,我看到你从包里掏的东西,虽然遮遮掩掩,但我看到了,你走后,我站起来又去翻了你的包,我猜得没错。”
苟洱似乎看到电话那头钱巍嬉皮笑脸的样子:“你真无耻、无聊,外加一个下流!”苟洱的话字字都往最脏的方向骂,可她的语气却像嘴里含了棉花糖,就像一个对着情人娇嗔,拿着粉拳砸铁肩的样子。
钱巍很受用:“还有吗?要没有了,你等会去那麦古塘一定要小心一点,你们局长安排你去,真是不安好心,那监狱建在山顶上,要是摔了下来,你……那座监狱算“文物”了,险就不说了,这些年里面设备陈旧,失修了,所以疑犯有机会逃出来,那地方已经逃了三四个人了,现在都没抓到,上面说拨款,拨他娘的几年了,也不见钱到哪里去了。我再说一次,你要是不小心就会掉下山崖的,你一定要穿平底登山鞋,再也不要像上次爆炸案那天穿小高跟了,那次算你狠,那么高居然没崴脚!”
苟洱听出了钱巍并无恶意,心里踏实了一点,她又在告诉自己:下次和他在一起,一定要再注意,再注意一点,以免被他又看出什么。随即她又一叹:哎,他足不出户,居然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自己跑案子那么辛苦,为何不多向他请教一下呢?人家毕竟是国安,手段和设备都比自己先进,刚叹完,她又纠结了:哼,我凭什么向你请教?谁知道你是不是白骨精给唐僧送饭,安了好心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