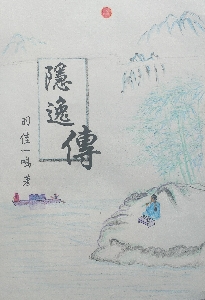黄昏的时候我独自爬到楼顶,一边往嘴里灌着罐装啤酒,一边远眺着夕阳滑落在高低起伏的楼群里。晚霞在西天渐渐消隐,夜色苍茫而来,像洪涛狂澜似的将整座城市淹没。我望着城市里亮起的万家灯火,不禁又想起了我的家乡。在漫漫的记忆中,家乡仿佛被一种魔力凝缩成了如梦似幻的风景。
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名字叫芦湾。它是一座不大不小的村庄,依偎着贾鲁河顺势仰首伸腰,形若飘带。村子里散落着高高低低的房屋,像是一朵朵野蘑菇。村子西侧被一条省级公路横贯,向南直通尉氏县城,向北可达古城开封。假如你路过芦湾,是不会太留意它的,因为在豫东平原上与它类似的村庄星罗棋布,它恰如大地上的野花野草似的朴实而又安静地存在着。
一幕幕记忆犹如鲜活的鱼在我的脑海中跳跃。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我身体瘦削,走起路来像是一根随风摇摆的弱草,更好笑的是我严重口吃。假如你是我童年的伙伴,一定难以置信此刻我会在你面前口齿顺畅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赵奶奶红润的脸庞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的笑容仿佛是滚烫的熨斗把眉头上的皱纹熨平,整个面孔显得既和蔼又健朗。她住在我家隔壁,我常常跑到她家去玩耍。她坐在木凳上对着一尊泥塑的佛像低声祈祷。红漆桌上的收音机播放着豫剧节目,咿咿呀呀的响着。一束阳光透窗而过,映照着一颗颗细微的浮尘。我站在她身旁结结巴巴地嘟囔。她扭过头说我前生一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被阎王爷手下的小鬼用剪刀铰掉了舌头,因此我才会口吃。
我听后惊惶不安,心脏像是一只野兔在胸腔里砰砰翻腾。她用右手摸着我的小脑袋说:“家树,你别害怕。佛祖会保佑你的,迟早有一天你会和正常的孩子一样顺顺溜溜地说话。”她又对着佛像低声祷告说:“弥勒佛啊,希望你大显神灵,保佑家树能够言语通顺!”
我瞅了一眼那尊佛像,只见一个袒胸露乳的胖和尚盘腿坐在桌子上,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它的两眼仿佛在瞄着我微笑。
“赵、赵奶奶,他……为——为什么……笑呢?”我吞吞吐吐地说。
“噢,弥勒佛看到人间众生欢喜的样子就笑了。”赵奶奶抿着嘴笑着说。
我听后懵头懵脑,抱起红漆桌上的收音机随手拨动着旋钮,嘈杂的音波在耳畔晃荡。
当我穿过村巷的时候,村民们总是拿我的口吃当笑柄。他们笑呵呵地问我说:“家树,你早饭吃了些什么?”
“馍……馍,洋、洋葱……炒——炒……鸡蛋,还有米、米汤。”这些话被我断断续续说完,好像是一堆积木城堡被我拆卸得七零八落。
人们望着我结结巴巴说话的傻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几乎笑断了腰。
孩子们追着我做着鬼脸,嘻嘻哈哈学着我说话的样子,笑喊着:“鸡蛋鸭蛋荷包蛋,孙家树是个大笨蛋!”
我与其他孩子说话的方式不同,我觉得这种不同像是河流里游着白鲦、鲇鱼、鲤鱼等不同的鱼一样稀松平常,也像是田野里长着喇叭花、地黄花、旋复花等不同的野花一样自然而然。我并不以为口吃是一种病,更没有意识到人们的嘲笑是一种耻辱,然而在众人眼里,与众不同好像便是一种疾病。为了摆脱这种疾病,人们吃相似的食物、穿相似的服装,并且学习同种语言与文字、遵循相近的生活规则。
人们不分朝夕,反反复复问我:“家树,你吃了些什么?”
我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回答。
那时候人们是那么关心我每天的饮食,像是当今的股民关注股市跌涨的行情。我像是一座小屋,里面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轻轻扣一下门扉,一阵笑声如火花似的迸射而出,让人们黯淡平静的生活闪起一道光芒、荡起一丝涟漪。我在人们的笑声中慢慢成长。我像是一块顽石,任凭时光肆意打磨。
我的口吃让父亲感到耻辱与愤怒。他从我身上丝毫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总觉得我不像是他的亲生儿子。在他眼中,我仿佛是一堆肮脏不堪的垃圾,他似乎恨不得将我扫地出门。
当我结结巴巴说话的时候,常常燃爆他的怒火。他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我的鼻子吼骂:“你这该死的笨蛋,闭上臭嘴当作哑巴,别丢人现眼!你出生那天老子如果知道你是这个样子,非把你扔进粪坑里淹死。”他说着,一口又湿又臭的唾沫飞溅到我的脸上,吓得我瑟瑟战栗。
我怯生生地仰望着他,只见他身材魁梧,体型肥硕,脸庞上嵌着一双白炽灯似的大眼睛,眼睛里放射出凶暴的目光。他的额头上烙着一点深褐色的疤痕,像是一颗黑痣,格外显眼。他上身穿着一件宝蓝色夹克衫,下身穿着浅灰色裤子,脚蹬棕色皮鞋。我最怕他的那双皮鞋——那是踢我屁股的武器,让我心惊肉跳。
“唉,孙福来,哪儿有你这样不近人情的父亲!”母亲叉着腰,两眼狠狠瞪着他说,“你小的时候还不如家树呢。你从小没爹没妈,是没人管教的野孩子,以后不准你再打骂孩子!”
母亲像是我的保护神,在父亲打骂我的时候她总是挺身而出保护我。这让我想起小鸡受到野狗侵害时母鸡振翅急鸣、摆出一副生死搏斗姿势的场景。保护孩子大概是世界上每个母亲的本能。
我抓着母亲的手臂战战兢兢,她将我紧紧揽在怀中。她凌厉的声势犹如一股汹涌的冷水扑灭了父亲嚣张的气焰。
“孩子他妈,我不给你吵架——我吵不过你。你年轻的时候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温顺。唉,如今怎么会变得像老虎一样凶猛!你把笨蛋儿子当作宝贝,处处袒护他,迟早要吃亏的。”父亲喃喃说。
他颓然坐在布沙发上,圆睁着眼睛,倾斜着身子从烟盒里掏出一根过滤嘴香烟,用打火机引燃后吸了起来,嘴里喷出一缕青烟。
母亲怒视着他,眼神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孙福来,我脾气变坏都是因为你——你脾气坏,我的脾气只有比你更坏才能不受你欺负。”
我仰脸望着母亲,见她脸上布满愠怒的神色。她的一双明眸如两潭清泉在眉毛下涌流。她上身穿着一件自己做的橘红色外套,看上去既得体,又时髦。她是远近闻名的裁缝,在芦湾的集市上开了一家裁缝店,为顾客修剪衣服。我们一家人的很多衣服是她亲手制作的。
据说母亲未出嫁之前性情温和,可是她嫁给父亲之后,受父亲坏脾气的影响,她的脾气变得暴躁易怒,与父亲隔三差五吵架。可见坏脾气与流行感冒类似,是一种病,是可以迅速传染他人的。
听人说母亲十七八岁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到芦湾老裁缝家学习裁剪手艺。有一天父亲遇到她后便对她着了迷。他经常呆在老裁缝家门口手里捧着几朵野花等候着她。她对他的涎皮赖脸讨厌至极,像躲瘟神似的躲着他。
那一年我姥爷患了偏瘫卧床不起。父亲借来一辆拖拉机把我姥爷送进了尉氏县城的医院,还鞍前马后伺候。不管我姥爷怎么撵他,他厚着脸皮就是赖着不走。他还偷偷去医院的收费室付款。
态度恰如巧克力,遇热变软,遇冷变硬。当某个人释放温情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往往会被软化。父亲的殷勤与执着让我姥爷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一天清晨我姥爷拉着我母亲的手说:“闺女,孙福来虽然平时吊儿郎当,在村子里口碑不好。我看他心地善良。瞧,这些日子他给我端茶倒尿,不嫌脏也不嫌累,对我比亲生儿子还孝顺。我看他是个好人,可以给你幸福。”
在姥爷的极力撮合下,母亲最终嫁给了我的父亲。
这些往事母亲绝口不提,像是密封在铁罐里的水果罐头。我却喜欢从街坊邻居们的口中撬开铁皮盖子偷吃那些“陈年罐头”。
我从街坊邻居们的口中听到父亲的很多往事。我的祖母在父亲三四岁的时候死于一种很奇怪的疾病,过了几年我的祖父因为患了严重痢疾而去世。父亲成了孤儿,他在乡亲们的照顾下长大成人。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村子里分田到户,他分到了一块田地,却懒得拾掇。俗话说:“人勤地不懒,人懒地长草。”野草长得郁郁葱葱,比庄稼还高,因此收成寥寥,他难以养活自己。他整日像叫花子一样四处游荡,蹭吃蹭喝。他好像是一条可怜巴巴又讨人厌恶的蛔虫寄生在村子里。
夜晚村子里放映露天电影,街道上黑压压的塞满了人。他像是一条泥鳅挤到人群里钻来钻去,偷摸大姑娘们的大腿,或者偷拧小媳妇儿们的屁股,吓得她们发出一阵尖叫。村民们把他当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有一天他的同龄人刘抗战结婚,到了晚上一群村民来闹洞房,让刘抗战脱光上衣,光着脊梁趴在地上当骡马让新娘骑。
父亲趁人不留意摸了一把新娘的屁股,这次他是摸了老虎屁股。新娘忽然一声惊叫跳了起来,一闪身狠狠扇了他一记耳光,又转身拿起桌子上的玻璃酒瓶向他摔去。他慌忙躲闪,酒瓶砸在门板上碎片四处飞散。
刘抗战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两手如钳子似的紧紧揪着他的一只耳朵,喊上一帮朋友一起把他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宣泄着怒气。他在众人的拳脚下像是一只干瘪的皮球在地上滚来滚去,发出一声声惨叫。
这样痛打仍然难以解恨,刘抗战燃上一根香烟说:“孙福来,你是个大流氓!我要让你永远记住新娘的屁股摸不得。听说古代要在犯人脸上刺字。今天我也要在你脸上做个记号。”刘抗战说着将火红的烟头擩在他的额头上,在惨叫声里烙下一个深深的疤痕。那个疤痕如同一枚印戳盖在他的脸上,印证了他不良的品行。
据说那天深夜父亲像是一只毛毛虫用双手缓缓爬回了家。他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沾满了鲜血与泥土。他蜷缩在床上,一阵凛冽刺骨的夜风灌进残破的窗户,他裹紧被褥,身体瑟瑟发抖。他迷迷糊糊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开上了一辆大卡车,在村巷里横冲直撞,可是猛然撞到一堵高墙,瞬间车翻人伤。他醒来之后伤口像是被疯狗咬啮似的疼痛,额头上渗出一滴滴冷汗。
他卧在床上痛苦嚎叫,街坊邻居们听到后推门进去,见他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大家纷纷谴责刘抗战下手过于狠毒,马上请来赤脚医生为他看病。大家又一起去找刘抗战评理,最后商定刘抗战承担大部分医疗费用。父亲养伤期间大家轮流照看。
过了两三个月父亲才能下床行走,当时正值春暖花开,田野中的麦苗蓬勃生长。他拿起镜子照到额头上那一点疤痕像是一张小鬼脸在讥笑他。他朝着镜子啐出一口痰,穿上布鞋推门出去。他并非是去找刘抗战报仇,养伤期间他思索出了一条致富的门路。
他从村口乘坐票车去了开封,到市区的皮鞋厂批发了一箱价格低廉的皮鞋。村子周边几个乡镇逢集的时候他便在集市上卖皮鞋。他成了一名鞋贩子,他热爱这份职业,也希望这份职业改变他的命运与生活。
那大概是一九八五年,村子里分田到户已有三四个年头,喂饱肚子的村民开始用口袋里的余钱购置一些“生活奢侈品”。手表啦,喇叭裤啦,皮鞋啦,这些新鲜事物势不可挡地涌进人们的生活。父亲靠着薄利多销的信条生意火爆,每次赶集都能卖出很多双皮鞋。
他的钱包渐渐鼓了起来,他不再四处蹭吃蹭喝。他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又买了一辆摩托车,春节前又新建了房子。他的日子原本像是一锅淡而无味的炖菜,鞋贩子这份职业像是食盐、酱油、香油等调料,将他的生活调和得有滋有味。
母亲嫁给父亲后,他好像是被《聊斋志异》里神通广大的陆判官割头换面了,变得越来越有经济头脑。他夏天租来大卡车向郑州、武汉、北京、天津等城市贩卖西瓜,秋天贩卖棉花。他靠贩卖这些农产品赚钱。
那是我五岁的一天,那天父亲喝得醉醺醺的,两颊泛出一片酡红,嘴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他站在门口,仰着头豪情万丈地向母亲嚷着说他决定在贾鲁河的旁边开办一家酿酒厂。他要收购村子里的麦子酿酒。他希望酿出的酒像贵州茅台酒似的驰名中外。
他歪坐在椅子上说着醉话:“我酿的酒要在全国千千万万个商店销售。我还要卖给美国人和苏联人,让他们扔掉威士忌和伏特加来买我的酒。”他说完耷拉着脑袋、挤上眼睛呼呼大睡。
母亲说父亲是在做白日梦,只有疯子才做白日梦。
次日上午父亲请来村里的几个建筑工匠商谈建酒厂的事情。他还请来王守道给酒起名字。
王守道在村子里做过多年会计。村里人都说他品行好、学问高。他瘦高的身材,头发斑白,双眼明亮而有神。他常年穿着一件蓝色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破旧的英雄牌钢笔——我偷偷摸过这支钢笔,笔尖钝拙,墨囊干涸,根本不能写字。据说它陪伴了他很多年,他舍不得抛弃。
父亲递给他一支烟,他噙在唇边,脸上浮出笑容说:“咱们村子很多孩子的名字都是我起的。这酒名啊,比起人名更难,叫着要响亮,人听着酣畅,自然就醉了。呃,天津有狗不理包子,名字虽然土得掉渣儿,吃起来却很香。我看这酒啊,就叫‘龟不醉’吧。”
“龟不醉?什么意思?”父亲问道。
“这酒啊,喝不醉的是乌龟王八蛋。”
父亲咧着嘴笑着说:“哎,喝不醉的人挨了骂,还不趁着酒劲儿扛着斧头、榔头把酒厂给砸毁。你再想个名字吧。”
王守道手指夹着香烟,皱着眉头思忖片刻说:“酒厂建在贾鲁河旁,我们酿酒最好用这河水。贾鲁河真是一条神河,据说河里住着龙王。从前村子里买不起药的人有了病到河边喝一瓢河水。嘿,这河水真有灵性,很神奇,很多人喝了它身体自然好了。用它酿酒,保准儿除病消灾,这酒就叫‘神河粮液’吧。”
“这酒名起得好!今天咱哥俩儿要喝两瓶纯粮酒,谁不喝醉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父亲眉开眼笑地说。
“我近期正在戒酒,这次要做缩头乌龟了。”王守道面露惭色。
“哦,你千万别戒酒,大家都像你一样戒酒将来我酿的酒卖给谁嘞!我看很多酒都说自己是历史名酒,有一大堆历史典故,还请你为神河粮液编造一些故事。”
故事好像是另一种白日梦。王守道沉思良久,讲道楚汉争霸时刘邦曾率领军队驻扎在芦湾,村民们向他进献神河粮液。刘邦用这些酒犒赏三军。将士们喝过酒之后像是打了鸡血,精神旺盛,意气昂扬,一举击溃了项羽的楚军。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仍对神河粮液念念不忘,将它列为贡品。王守道又将神河粮液与曹操、赵匡胤、朱元璋攀上关系,为它编织历史的光环。我在旁边仔细聆听,听得稀里糊涂。他所说的那些人物,我一概不知。他们也许生活在距离芦湾很远的村庄,或者生活在很遥远的年代。
过了一段时间,麦田由一片翠绿被阳光渲染为一望无垠的金黄,麦穗随风摇摆,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贾鲁河被麦田映衬,河水静静流淌,如一条长臂拂过村庄的边缘。
那天酒厂大功告成,有人站在屋顶燃上一挂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阵乱响。父亲摆上几桌酒席感谢建筑工匠。
他雇佣了一名老酿酒师以及六七名工人。他还买了一辆面包车,与雇工双喜一起开车四处接洽业务。他强烈要求母亲关闭裁缝店,帮他料理一些琐事。母亲原本不同意,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她还是应允了。那天她流露出眷恋不舍的神情,缓缓锁上裁缝店的门,在门上贴上一张写着毛笔字的纸条。
酒厂好像是一只大蛤蟆趴在村子南侧,对望着贾鲁河。里面盖了几座房屋,屋顶上覆盖了一层灰色的石棉瓦,屋墙上竖着一根冒着浓烟的大烟囱,像是大灰狼的尾巴。每次我溜进酒厂的时候刺鼻的酸味儿扑面而来,几乎把我熏倒。只见几个叔叔、伯伯们在烟雾腾腾的屋子里忙来忙去,他们根本没有功夫与我玩耍。
有一天父亲对王守道说:“万事开头难,这酒生产出来了,现在销路却打不开。”
王守道一只手捏着烟卷,思考片刻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你要重视宣传。最好花些钱,去县城电视台做广告。”
父亲听后豁然开朗,拍着大腿说:“好主意,我明天就去县城!”
几天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神河粮液短短的广告。这条广告真像是一剂药,很快治好了酒厂销路不畅的病。
有一天父亲踌躇满志地说:“咱们要向全国各地运送千千万万吨酒,挣钱挣到两手发抖。”
母亲坐在凳子上喝着水,漫不经心地说:“哎,孙福来,你天天做白日梦,满嘴跑火车!”
我的视线从电视屏幕转向父亲的嘴巴上,却没有看到哐当哐当的火车冒着黑烟在他嘴里奔跑。我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说他满嘴跑火车。
父亲腾出一间干净的小屋子作为办公室,摆放上办公桌与黑皮沙发,还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当时那是芦湾唯一的电话。他经常一只手夹着烟卷,一只手握着话筒打电话。他瞥到我弯着腰在墙角捉蛐蛐儿便大声吼叫:“喂,你这个笨蛋,在这里碍手碍脚的,影响我工作,赶快滚蛋!”
“孙福来,你不配做父亲!”母亲站在门口满腔愤懑,绷着脸说,“你对自己的孩子一点儿不关心,孩子的生日竟然忘记了。你配做父亲吗?将来你老了,腿脚不灵便,躺在病床上又脏又臭。家树,到时候你别照顾他,让他自生自灭。”
“哎,孩子他妈,你把我说成大坏蛋了。家树也是我的儿子,我怎么会不关心嘞!我老了不依靠他,我依靠我女儿家华。”
酒厂里的叔叔、伯伯们听到后面露笑容,用衣袖抹着脸上的汗水。阳光倾洒在他们身上,仿佛给他们浇上了一层铜黄色的油漆。
双喜笑着说:“福来大哥,嫁出去的闺女是泼出去的水。家华迟早要嫁人的,成了别人家的人。你老了还得依靠家树。”
“等我老了住养老院,我谁也不依靠。”父亲说着瞪了我一眼。“你呀,长大后别混成叫花子四处讨饭吃。”
“孙福来,你就这么瞧不上你儿子吗?你对孩子没有一点儿信心,有你这样的父亲吗?”母亲反问说。
“从他身上我看不到我的气概,哪儿像我的儿子!”
“孙福来,你有什么气概?家树不是你的儿子吗?”母亲提高嗓音问道。
在父母的争吵声中,我拔腿跑到酒厂外的菜园子里去玩耍。那里是我的一片小小的乐园。
菜园子占地有一座屋子那么大,四周被交叉错杂的树枝做成的篱笆围着。园子里的蔬菜我大都叫得出名字。那枝茎缠绕在木架子上、开了一层紫色小花儿的是豆角,那从绿藤上垂下像长手臂似的果实的是黄瓜,那一个个像小红灯笼似的是西红柿。
我最喜欢篱笆边的那几株向日葵。我常常坐在青草上仰望着它们。向日葵细高的个头,圆圆的脸庞,太阳跟着它们扭头的方向移动着火红的躯体。太阳好像是向日葵放飞在天空中的一只金灿灿的圆风筝,随着一缕缕五色阳光的伸缩而改变方向。
我痴痴地问向日葵:“向日……葵,我、我问你,我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在阳光下向日葵的脸庞上好像闪烁出一丝微笑。它们沉默无声,在风中微微摇动着身体。它们是哑巴,根本不会回答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