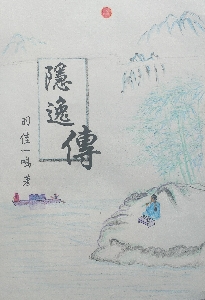有一天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的桌子上做作业,黄狗温顺地卧在我的脚下。我握着铅笔在作业本上照着黄狗的样子乱画,画得歪歪扭扭,在旁边写道“我是一条小狗。”
“我画得像你吗?”我将那张画从作业本上撕下来摆在黄狗面前。
它警觉地瞄了一眼画像,见不是馍头或骨头,仍然耷拉着脑袋伏卧在地上。
我轻轻踹了它一脚说:“坏蛋,这画的就是你。”
它起身向我汪汪的叫了几声,像是与我吵架。当我准备再次抬脚踹它时,它紧挨着我的脚卧在地上,一副涎皮赖脸的样子,让人不忍心伤害它。
我不经意瞥到抽屉的缝隙里露出父亲那只棕色的皮包。我猜想父亲今天走得匆忙,忘了带它了,平时他总是带着它的。我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便好奇地将它打开,只见里面有香烟盒、打火机、电话簿、钱包等,竟然还有一只精美小巧的红色包装盒。
我把那个包装盒托在手心里上看下看,然后掀开盒盖,发现里面放着两枚耳坠。耳坠的上端是一根短针,中间悬着一条细小的金链子,下端缀着一颗包着金边儿的紫水晶。紫水晶莹亮华美,犹如两颗眼睛,闪耀着紫光。我将它放在手心里细看,心想母亲的生日越来越近了,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想到父亲如果知道我偷偷打开他的皮包,他一定会雷霆大怒。我赶紧将耳坠小心翼翼地装进盒子里,将皮包放回原处。
接下来的几天紫水晶耳坠的光芒一直摇摇晃晃在我眼前闪耀。
一天晚上我与家华坐在布沙发上看着电视。灯光下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为家华做一件色彩鲜艳的外套。
“妈妈,我怎么从没见你戴过耳坠?”我走到缝纫机前说。
“瞧,我两只耳朵上很早就打了耳孔,年轻时戴过耳坠,不过很多年不戴了,之前的耳坠早丢失了。”母亲说着两脚继续踩着缝纫机的脚踏板。
“爸爸会给你买耳坠的。”我神秘兮兮地说。
“唉,他没有那份儿心。”母亲的手停在针头旁,摇着头说。
“妈妈,你生日那天爸爸会给你一场惊喜的。”我说。
“我不要他的惊喜,他不给我惊吓就好了。”母亲流露出惘然的神情。
“妈妈,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买耳坠。”家华说。
“傻孩子,我不喜欢戴耳坠,也不喜欢戴戒指,戴这些东西太麻烦了,一不小心还会丢失。”
我本想告诉她说我在父亲的皮包里发现了两枚紫水晶耳坠,当我想到父亲用皮鞋踹我的时候,便欲言又止了。
我期待着父亲给母亲一场惊喜,然而她一语成谶,父亲给她的不是惊喜,而是一场惊吓。
过了几天,郑老师刚登上讲台,我发现她的耳朵上戴着一双紫水晶的耳坠。我惊诧地望着她,望着耳坠在她的耳垂下面轻轻摇曳。它竟然和我在父亲皮包里发现的耳坠一模一样!
“郑老师戴的耳坠真漂亮。”刘亚军小声对我说。
郑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念着课文。我心不在焉,思绪翻飞。
我突然想到她的耳坠有可能是父亲送给她的,但是转念一想,他们鲜有来往,彼此只是认识,父亲是不可能送给她礼物的。
下课之后我问刘亚军:“亚军,你之前见过郑老师耳朵上那一双耳坠吗?”
“没有,她一直戴着银耳环。今天她戴的耳坠应该是新买的,第一天戴在耳朵上。”
“你相信世界上有和它一模一样的耳坠吗?”
“当然有啦,喏,你的文具盒,文具店里和它一模一样的多着嘞。耳坠嘛,到城里卖首饰的商店,一模一样的一大堆,任你挑选。”
刘亚军的一番话消除了我内心的疑虑与纠结。我想郑老师耳朵上的耳坠是她在县城的首饰店买的,恰巧与父亲皮包里的同款。
我心里仍然期待着母亲生日那天父亲会给她一场惊喜,想象着父亲将皮包里的那双耳坠戴在母亲的耳朵上。
薛大攀仍然像是一张狗皮膏药似的紧粘着郑老师。他常常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却对他不理不睬的。人们都说他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劝他不要作践自己。他却痴心不改,年复一年地追求她。
有一天他厚着脸皮将一台录音机送给她。那是一台黑色的盒式录音机。她莞尔一笑将它提在手里说:“薛大攀,我们教室需要一台录音机,这算是你捐献给小学生们的。我替孩子们谢谢你了。”
“郑敏,你给谁用我管不着,你也别谢我。我很高兴。”薛大攀笑眯眯地说。
“我这是借花献佛。大攀,你可以选几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放给孩子们看,算是做件好事。”
“你推荐几部电影呗,我牢记着,晚上在操场上放映。”
“这类电影很多,例如《鲁冰花》、《妈妈再爱我一次》、《豆花女》。”
“哦,我记住了。我一会儿去县城找一下影片,下周开始放映,到时候你组织一下学生。”
上课的时候郑老师经常将朗读课文的磁带塞进录音机的磁带仓里,随着磁带的旋转抑扬顿挫的录音从扬声器里播放出来。
有一次临近下课的时候她用录音机给我们播放了一首外文歌曲。当我正歪着脑袋听得如痴如醉的时候,下课的铃声突然响起。她摁了一下录音机开关的按钮,啪嚓一声歌声戛然而止。那些旋律却像是一群花蝴蝶围绕着我漫天飞舞。
她提着录音机,掂起讲桌上的课本离开教室。
我起身追上去问她:“郑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刚才录音机播放的那首歌曲的名字。”
“这是一首英语歌曲,名字叫Yesterday Once More,翻译成汉语是《昨日重现》。”她微笑着说,她耳朵上的那一双紫水晶耳坠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
“噎死他……玩死猫……”我模仿着她的发音说。
她望着我咯咯笑了,说:“以后你学英语了就会读了。”
那段时间薛大攀常常将白色的电影幕布悬挂在操场上。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搬着凳子涌向操场。他端坐在放映机前满脸笑容,为我们放映很多感人的电影。
薛大攀突发狂想,要在芦湾开一家小电影院。他在集市上租赁了一间平房,里面简单用白灰粉刷了墙壁,排上六七排红漆木长椅,又在门口贴上几张电影海报,就这样小电影院草草开业了。
开业当天村民们可以免费看电影,房间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他坐在放映机前兴高采烈,梦想着将来要开一家大型电影院,可以容纳很多人,让全村人对他刮目相看。
第二天小电影院开始收取门票,村民们大都坐在家里看电视节目,不来捧场了,屋子里稀稀落落坐了七八个人。
马宝财坐在第一排椅子上高声叫嚷:“六根指,放毛片呗!”
“我这里真没有毛片。”
“你一个人关着门在家里偷看,好东西一个人藏着。”
“我这里根本没有毛片,想看毛片滚蛋!”
“哼,把门票钱退还给我,老子不看了。”
薛大攀的电影院开业不久由于入不敷出倒闭了。
村里有人办喜事请薛大攀放映电影,他像之前一样黄昏时将幕布悬挂在街头,在桌子前调试机器设备。当夜色苍茫时开始放映,然而幕布前的观众少了很多,再没有从前那种人声鼎沸的场景了。
我搬着凳子走到薛大攀身旁,他正在操作着放映设备。
“大攀叔叔,我要向你学习放映电影。”我好奇地望着桌子上的胶片。
“唉,你好好学你的功课。这几年年轻人大都去城市打工了,村子里的电视机也多了,来看露天电影的人就少了,我也快下岗了。”他流露出落寞的神情。
有一天数学老师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数学应用题。我抬头望到黑板上写着“动物园一只大象2天吃420千克食物,一只熊猫4天吃70千克食物。一只大象的每日食量比一只熊猫多多少千克?”
吴老师写完那道题将粉笔抛在讲桌上,目光扫视一下教室说:“同学们计算一下,稍后我找人回答。”
我握着铅笔一筹莫展。那道应用题像是多条绳子缠绕而成的死结,我死活解不开。
“孙家树,一只大象的每日食量比一只熊猫多多少千克?”吴老师嗓音响亮,他冷峻的目光刺得我浑身发疼。
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抬头望着黑板。
“呃……180千克。”我摸着脑袋随口说。
“噢,我们可以计算出一只大象每天食量210千克,一只熊猫每天食量17.5千克,210千克减去17.5千克等于192.5千克,少的那10多千克哪里去了,是不是你偷吃了!”
同学们哄堂大笑,脸上笑开了花。
那天下午放学,我和刘亚军到沙岗上玩耍。我们用沙土堆了一座城堡之后坐在城堡旁嘴里嚼着泡泡糖,比试着谁吹得泡泡大。
“家树,昨天我和哥哥打架了。”刘亚军说。
“为什么?”
“哎,我把哥哥课本上的那一张彩页撕掉了——上面印着赵州桥,我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哥哥看到后气得发疯,就追着打我,我吓得四处逃跑。”
“赵州桥?”我茫然地问。
“嗯,它是一座大石桥,却千百年也没有倒掉。你听说过苏州园林、悉尼歌剧院、法国埃菲尔铁塔这些建筑吗?”他兴致勃勃地说。
“没有。”我摇着头说。
“我从各种书本上看到的。我长大后想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惊人的建筑。”他用率真的口吻说。
“亚军,你的梦想真好。”
夕阳像是将一大桶番茄酱倾倒在沙岗上,闪耀着酱紫色的余光。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映照着村庄。两只乌鸦在不远处的树上嘎嘎叫着。
“亚军,听,这是什么声音?”我突然侧耳聆听。
“乌鸦的叫声。”
“不是,你听听,像是乐器的声音。”
微风在沙岗上吹拂,送来了一阵铮铮琮琮的旋律,宛如湍急的流水声。
“呵,是有人在弹吉他。”我歪着脑袋用两耳去捕捉微风中的旋律,露出惊喜的表情。
“吉他?你怎么知道?”
“我在电视里听到过它的声音。你听,太好听了——铮铮,铮铮!”
“哦,这声音是从学校发出来的,我猜是哪个老师在弹吉他。”
“不是,这声音是从槐树林里传出来的,不信你再听听。”
“哦。”刘亚军的耳朵向着槐树林的方向倾斜。
“走,咱们去瞧瞧!”我将泡泡糖吐在沙岗上。
橙红色的夕阳映衬着一树树洁白粉嫩的槐花。我们循声向着槐树林奔跑了过去。那歌声越来越清晰。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声在浓郁的槐花香气里起起落落。
我们望到一个年轻人站在槐树下弹着吉他。他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瘦高个儿,头发略长,下巴上蓄着短胡子。他微闭着眼睛,抱着一把吉他边弹边唱,一副深情而潇洒的样子。在他手指的拨动与按压下吉他变成了一个鲜活的精灵,时而像淙淙的溪流吟唱,时而像奔腾的浪涛喧哗。
“他是养蜜蜂的。喏,那树下是一片蜂箱,还有两个帐篷。”刘亚军指着槐树下的那一个个木制蜂箱说,“瞧,那儿有很多蜜蜂,嗡嗡嗡嗡。咱们最好不要靠近它们,它们蜇人。”
只见槐树下摆放着很多蜂箱,两顶军绿色的帐篷搭在蜂箱旁。一对中老年夫妇模样的人在蜂箱旁忙碌。我猜想他们是那个年轻人的父母。
那个年轻人唱着歌。我沉浸在他的歌声里。
“嘿,家树,你怎么了,看你变成一个木头人了。”刘亚军大声说。
我很想走近那个年轻人抚摸一下吉他,并奢想让他教我弹吉他。
“你甭唱歌了,来帮一下忙。”那个中年妇女喊道。
他猛然停止唱歌,露出扫兴的神情,抱着吉他向蜂箱走去。
“家树,咱们走吧,天黑了。”刘亚军说。
“嗯,我真想有一把吉他。”我说。
“有了吉他你也不会弹。”
“不会可以学习嘛。”
吃过晚饭后母亲与家华看着电视。吉他的旋律在我耳边挥之不去,我嘴里念叨着:“铮铮,铮铮!”
“家树,看你疯疯癫癫的,怎么了?”母亲说。
“妈,这是吉他的声音。”
“吉他?”
“我下午看到一个大哥哥在槐树林里弹吉他,我也想有一把吉他。”
“噢,过段时间我给你买个新书包。”
“我不喜欢新书包,我喜欢吉他。”
黄狗趴在院子里昏昏欲睡,我轻轻踢了它一脚走出院子。
夜空缀满繁星,星光将黑暗的夜色烘染成朦胧的灰色。家家户户已经关上了大门,从窗户里漏出电灯的光线。村巷上冷清无人,我踩着黝黑的路面走着。两只野猫在夜色中窜动,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
当我走近槐树林的时候望到一盏电灯挂在槐树下,光线照得四周白花花的。三个人正围着一张小木桌吃饭。
那个年轻人回头看到我,边嚼饭边说:“小孩子,你来这儿干嘛呢?”
“大哥哥,我想向你学习弹吉他,你弹得真好。”我走近他说,望到那把吉他斜放在他身后的小凳子上。
“你这孩子嘴上沾了蜂蜜了,真甜。来,我教你!”他说着咽下口中的饭菜,顺手拿起吉他。
“好呀。”我高兴得要跳起来。
“教你之前你要让我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孙家树,你呢?”
“我叫大哥哥。”
“大哥哥?”
“嗯,我姓大,名字叫哥哥。来,我教你,不过弹吉他一朝一夕根本学不会。我先给你简单讲一下每根弦的作用,再慢慢教你弹奏的方法。”
那对中年夫妇坐在饭桌前笑得前仰后合,说:“小峰,你真适合当音乐老师。”
“你叫小峰,以后我叫你小峰哥哥。”我说。
“噢,你真聪明。”
夜渐渐深了,村子越来越静谧。繁星装点在天幕上,犹如一盏盏小灯笼在夜幕上闪烁。
在电灯的光线下,小峰哥哥耐心地教我弹吉他。铮铮的吉他声在槐树林中回荡。
他露出疲倦的神色,打了个哈欠说:“我明晚再教你。今天太累了,该睡觉了。”
“嗯,我想弹一次。”我说。
“你回家睡觉吧!”他说着,将吉他放在帐篷旁。
“小峰哥哥,你家在哪里呢?”
“安徽。”
“哦,应该离这里很远很远。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当然了,我大江南北都去过。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去油菜花开的地方;槐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去槐花开的地方;葵花开的时候,我们去葵花开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去了哪儿,也记不得那些城市、乡镇和村子的名字。”
我在黑魆魆的村巷里奔跑,嘴里哼着歌,惹得几户人家的狗汪汪的叫着。
当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母亲拿着手电筒迎了过来,耀眼的光束照在我的脸上。
“你这疯孩子,干什么去了?”母亲的神情焦急而气愤。
“我去学弹吉他了。”我兴高采烈地说。
“你跟谁学的?”
“跟小峰哥哥学的。”
“小峰哥哥?咱们村子里好像没有这个人。”
我将事情给母亲讲了一遍,她的手摸着我的脑袋说:“我还以为你失踪了。”
那几天放学后我就跑到槐树林里找小峰哥哥。上课的时候我总是心猿意马,想着弹吉他的事情。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一道应用题让我回答,我仍然回答错误。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