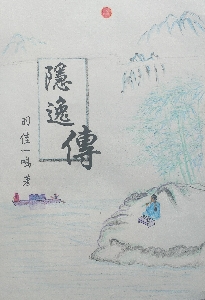西瓜即将成熟的时候雨季袭击了村庄。一场暴雨过后,贾鲁河的水势凶猛如虎,吞没了杂草丛生的河滩。村旁三四个池塘池水满溢,一片汪洋。
太阳出来的时候天气酷热,村子里却隔三差五停电。电影放映员薛大攀说县城的火电厂发电量不足,就暂时停掉农村的电,让城里的单位、医院与学校优先使用。烈日下的村庄像是火炉似的炙热,好像要把在院子里啄食的柴鸡烤成烧鸡。屋子里的电扇瘫痪了,闷热如蒸笼,人们聚集在街头的树荫下摇着蒲扇纳凉,聊些家长里短。
我和一群孩子赤条条的在池塘里洗澡。我不会游泳,只能像蛤蟆一样匍匐在浅水中。
三个年龄稍大的孩子水性较好,犹如三只野鸭子在池塘里游泳,扑通扑通,翻腾出一朵朵晶莹透亮的水花。
“我也……也——”我望着他们喊道。
“你也……也——你爷爷怎么了,你爷爷是大乌龟!”一个孩子没等我说完便笑嚷着。
“我——我也……想学游、游泳。”我的脸憋得通红,自己想说的是“也”,而不是“爷”。我吞吞吐吐地将一句话说囫囵。
“好,我们来教教你。”他们笑喊着向我游了过来。
我高兴地用手掌在水面上击出一道水浪。
他们游到我身边,一个孩子拽着我的左手,一个孩子拉着我的右臂,第三个孩子托着我的脊背。他们用手与脚矫捷地拨动着水面,身子猛然犹如轻快灵巧的橡皮船漂浮在水面上。
“学着我的姿势,手臂伸直——开始蹬腿!”一个孩子说。
我跟着他们向深水处游去,一条顽皮淘气的小鱼撞了两下我的腿肚。他们的拉力与水的浮力把我带到池塘中央。我笨手拙脚地学着游泳,扑腾出一朵朵水花,身子却仿佛是沉甸甸的石头,总是不听使唤,慢慢向水下坠落。
“大笨蛋!”一个孩子讥笑说,他说着将一层水花拍打在我的脸上。
“孙家树,叫我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一个大孩子喊着,“你不给我叫爸爸,我就让你喝脏水。”
我红着脸,呼吸急促,用手掌狠狠划动着水面,身子半浮半沉。
池水像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龇牙咧嘴,要将我吞进肚子里。
那个大孩子高声嚷着:“叫我爸爸,叫我爸爸!”说着一只手使劲儿将我的头向水中按压。
另外两个孩子一边用手推搡我,一边喊着:“快叫爸爸,快叫爸爸!我们都是你爸爸,我们都是你爸爸!”
“我今天在池子里撒了两泡尿,你喝池水就是在喝我的尿。”一个孩子笑嚷着。
我始终不向他们叫爸爸。我对“爸爸”这个词语感到既淡漠又恐惧,却不愿辱没它。
我在水中惊惶而愤怒,慌乱地挣扎着四肢,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口脏水,竟然将卡在喉咙里的一根水草吐了出来。
“嘿,孙家树嘴里吐出了一根草,他成了吃草的绵羊了!”孩子们欢笑着望着我。
在草地上放羊的朱老兵听到孩子们的喧闹声一瘸一拐地跑了过来。他伫立在岸上向池塘张望。他用力甩开皮鞭,噼啪一声锐响,如同一声响雷,将孩子们的视线扭转到他身上。
“喂,你们这群娃娃们别胡闹了,照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们三个捣蛋鬼,快把孙家树拖上岸!”他声若洪钟,用命令的语气厉声高喊。
据说朱老兵年青的时候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左腿受了枪伤,成为瘸子。他回到村子里养伤,依靠着微薄的抚恤金生活。他曾经娶过老婆,可是婚后不久,他的老婆嫌弃他残疾无能,跟经常来村子里的剃头匠私奔了。他羞惭而愤恨,从此搬出村子,孤身一人住在苹果园的一座小屋里。他喂养了几只羊,经常在野草地上放羊。
那三个孩子被朱老兵的声势威慑着了。他们一起扑腾着水浪把我拖上池塘岸边。
我躺在地上头昏脑胀,不停地喘着粗气,嘴里一个劲儿地向外吐脏水。
孩子们紧紧围着我,希望看到我的嘴里能够吐出一只蝌蚪或者一条小鱼。
朱老兵回头远远地看到一只羊正要越过菜地的矮篱笆去啃青菜,他高声喊着:“咦,你这只该死的公羊,别糟蹋了青菜!”他抡起鞭子歪歪扭扭地跑了过去。
阳光灼热而刺眼,几只蝉在杨树上扯着嗓子鸣叫。
“呵,大家瞧啊,一只蚂蝗正咬在孙家树的大腿上吸血!”一个孩子叫嚷着。
我低头看到一只黑褐色的蚂蝗正紧紧叮在我的左腿肚,如一枚尖利的钉子钻到我的腿肉里。我赶忙用手拔着它。它身体柔软粘滑,怎么也拔不出来。
有一个孩子突然说:“前几天一只蚂蝗咬着我的腿,我拿着鞋子摔打才把它打出来。”他说着拿起旁边的一只塑料凉鞋向我的左腿上用力摔打,啪啪啪啪,摔打了十多下。
我的左腿上的血管似乎要胀裂迸血。我哀叫着,眼里噙满泪花。
“你忍着点儿,再打几下它就出来了。”那个孩子又狠狠地在我的左腿上摔打了几下。“嘿,真出来啦,它喝了不少血——该死的吸血鬼!”
孩子们发出一阵欢呼声,将那只蚂蟥抛在池岸上。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为我做一条卡其色短裤。她的两脚踩着脚踏板,一只手轻轻抽着布料,咔哒咔哒的声音在房间里振荡起伏。
家华坐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看着动画片《葫芦兄弟》。
母亲转过头见我蔫头耷脑的样子,问道:“家树,今天怎么了?”
我走近母亲,眼神里蓄满了幽怨。我伸出左腿,眼泪一下子滚落了下来。
她一眼看到我左腿上一片红肿,露出惊愕而气愤的神情。
“家树,今天是谁欺负你了?给你打成这样。我带你去评理!”
“蚂——蚂蝗……”我哭着说。
我担心母亲去找人评理,为了我又要和人吵架,就没敢把那三个大孩子欺负我的事情告诉她。
“唉,你又偷偷去池塘洗澡,那里水深危险,水又脏,而且蚂蝗多,以后不准你去池塘洗澡了,再去的话我拿扫帚打你的屁股。”
家华拉着我的手,盯着我的左腿,稚声嫩气地说:“哥哥,前几天在菜园子里咱俩遇到一条大青蛇,你一点儿也不害怕,怎么会害怕蚂蟥呢?”
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花露水用棉花团在我的左腿上抹擦,淡淡的清香在屋子里弥散。她又将刚刚做好的短裤让我试穿。
“妈妈,我很想要一条花裙子。”家华说。
“好,我给你做一条连衣裙,再绣上一朵红荷花。”
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太阳像熊熊炭火似的烘烤着大地,蝉趴在树枝上不停地嘶喊:“热——热——”
我们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着西瓜,突然听到一位妇女在街上高亢而凄惨的呐喊:“救人啊,救人啊,快到池塘救人啊!”
村民们纷纷向池塘方向跑去,边跑边嚷:“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唉,池塘淹死孩子了,淹死了三个!”
“哎呀,谁家的孩子,这么命苦!”
白花花的阳光耀人眼目,靛蓝的天空上堆积着几朵白云,犹如一具具惨白的死尸悬浮在空中。
整个村庄好像是沸腾的油锅,充斥着紧张而惶悚的气氛。
当我跟着母亲来到池塘边的时候,四周已经挤满了人。我远望到三具孩子的尸体静静地躺在草地上——他们正是前些日子欺负我的那三个孩子!家属在尸体旁嚎啕大哭。我睁大眼睛,露出惊恐的神情。
据一个目击者说他们在池水里打闹,一个孩子在水里被推翻后向水底沉沦,另外两个孩子去施救,三人却深陷旋涡,难以脱身,很快被池水吞噬了。
村子里几个水性较好的年轻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的尸体打捞出来。
一辆急救车鸣着车笛穿过草地停在池塘附近。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白大褂的男医生。他们拿着听诊器弯着腰在三具尸体上测一测呼吸,摸一摸肚子,又掰了掰眼睛。
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希望那三个孩子在他们的抚弄下能够睁开眼睛,能够慢慢站起来。
“大夫,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孩子,求求你们!”家属们抹着眼泪跪在地上哀求着。
“他们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也无能为力。”医生表情严肃,说完转身离开。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的孩子是可以被救活的!”家长们哭喊着,紧紧拉住医生的手。
“唉,我们已经尽力了。”医生声音低沉。
在家属们的嚎啕痛哭中,三具尸体被装进了三口杨木小棺材里,被拖拉机拖到了乱葬岗上。
老人们说那三个孩子已经变成狰狞可怕的水鬼,在池塘里等待洗澡的孩子,然后引诱孩子们落水淹死,这样他们才能投胎转世,从此村民们严禁自己的孩子到池塘里洗澡。
我总是设想,那天那三个孩子在池水中欺负我,如果没有朱老兵搭救,我可能会被淹死。唉,人的生命好像是飘在空中的肥皂泡,死亡是一个爱抓肥皂泡玩耍的孩子。死亡抓到了谁,谁就会在这个世界上瞬间破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