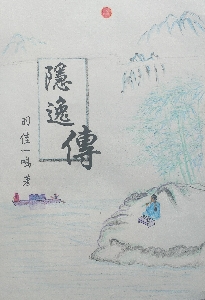秋天匆匆过去,冬天来临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寒风像是一位长着千头万臂的理发师,手持千万把锋锐的剪刀,将树木满头的黄叶纷纷剪掉。屋檐下的燕子没有了踪影,老师在课堂上说它们去南方过冬了,等到明年春风会把它们送回来;蛇、蛤蟆、刺猬等小动物已经钻进土洞里了。老师说它们开始冬眠了,要睡上整整一个冬季,到了春天,轰轰隆隆的春雷将会把它们唤醒。
我想,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像是人类似的有胳膊有腿,它们在大地上来回奔跑。它们跑到哪里,哪里的气候与生物便归他们统治。对于芦湾的人们来说,春天是属于麦子的,人们为麦苗浇水施肥;夏天是属于麦子与西瓜的,人们收割麦子、颗粒归仓,采撷西瓜、卖瓜和吃瓜;秋天是属于玉米与棉花的,人们掰玉米、晒玉米,摘棉花、剥棉花、卖棉花;冬天田野空旷,天寒地冻,人们暂时不用在田野里忙碌,在家歇息或者干些零碎家务。冬天是属于人们自己的,是享用果实的季节。人生好像被四季瓜分,被土地束缚,被农作物羁绊,这便是很多人一生的写照。
初冬时节,村民们将一筐筐红薯储藏在地窑里,又将大白菜、冬瓜与萝卜整整齐齐堆在院子里,用厚厚的麦秸掩藏起来,以起到保暖保鲜的作用。这些蔬菜是我们过冬的美味佳肴。
村民们从集市上买回棉鞋、棉裤与棉袄,在街头遇见熟人交谈说:“今年应该是寒冬。瞧,刚刚立冬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一度,赶紧买厚衣服过冬,别冻坏了身子。”
有一天傍晚北风凛冽,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父亲在县城应酬生意没有回家,母亲坐在椅子上织着毛衣,我和家华看了一会儿电视节目便睡着了。
次日清晨,村庄、田野、河流全被茫茫白雪覆盖,恍如银雕玉砌的世界。
母亲洗漱后拿起铁锨与扫帚在院子里铲出一条通路。当她扫到大门口的时候发现门口的积雪已经被清理了,还堆着两个雪人。
她望到二傻正弓着腰在街道上扫雪。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二傻属于那种下了雪恨不得把整个村庄的雪都清扫的人。
“二傻真勤快,这一条街上的雪都被你清扫了。”母亲说。
“天没亮的时候我就起床了,边扫雪边在街上拍雪人。家树和家华见了雪人一定喜欢。”他的嘴里哈出一团白气,满脸憨笑。
“你呀,真是一个长不大的大孩子!”母亲笑着说。
天晴的时候,清晨的天色蔚蓝而朗润,如一块宏大的蓝宝石嵌在村庄之上。而那天是雪天,清晨的天色灰蒙蒙的,空中聚集着几朵阴云,好像一片片活泼顽皮的雪花歪坐在云上,随时会从云朵上跳下来。
村民们起床后纷纷烧火做饭,一道道青烟从烟囱里爬出来,扭着弯弯曲曲的肢体,仿佛是在雪景中翩翩起舞,却被一阵寒风吹散在半空。
薛老六穿着厚棉袄,两耳戴着耳暖,沿着雪路缓慢地推着三轮车吆喝:“卖豆腐,新磨的豆腐嘞!卖豆腐,新磨的豆腐嘞!”他的吆喝声在雪天显得更加清晰嘹亮。
厨房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切菜声,稍后一阵噼里啪啦烹炒声传了过来,一股醋熘白菜的味道儿弥漫在空气里。
母亲腰里系着花布围裙,手里拿着油腻发亮的锅铲在院子里喊着:“家树,家华,你兄妹俩赶紧起床,太阳晒着屁股啦!”
“今天是雪天,哪里有太阳啊!”家华穿着红棉袄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妈,今天是星期天,我不上课,我要睡懒觉。”我在被窝里向着窗外说。
“小懒虫,赶紧起床,一会儿饭菜就凉了。”
“妈妈,还是我勤快。这棉袄是我自己穿上的,好看吗?”家华笑着说。
“哎,好看。家树,瞧,你妹妹多勤快,还自立自强,你这懒哥哥落后了。”
“哥哥,快些起床,咱俩一块拍雪人去。”家华向着我的卧室喊着。
“二傻已经在街上拍好两个雪人了。”母亲随口说。
“好呀!”家华说着跑了出去,看到门口果然站着两个雪人。“哎呀,哥哥,快些起床看看雪人吧!”
“咦,家华,你这傻丫头,快回来,吃过早饭再出去!”母亲向着家华喊道。
我慌慌忙忙穿上棉袄与棉裤,趿拉着棉鞋出了门。
“别急,天冷,穿上棉鞋——傻瓜,你急得棉裤穿反了,瞧你这傻样子!”母亲看着我哭笑不得,把我拉回屋子里给我重新穿衣服。
我低头看了看,我确实穿反了裤子。裤子的前面鼓鼓囊囊的,本是屁股的位置,难怪刚才走起路来别别扭扭的。
“哥哥,你裤子穿反了,屁股长到身子前头就好了。”家华笑嘻嘻地说。
吃饭的时候,母亲给我和家华讲了一个懒孩子的故事。
母亲讲道:“从前啊,有一个懒孩子——很懒很懒的孩子。他懒得穿衣服,懒得吃饭。有一天他妈妈要出远门,怕他饿肚子,临走的时候他妈妈把炕好的一张大圆饼套在他的脖子上说:‘孩子,你要是饿了,就咬这个大饼吃。’嘱咐后,他妈妈走了。过了几天后她回来,发现这个懒孩子竟然活生生地饿死了。原来懒孩子只啃了嘴巴下面的饼,其余的饼他懒得去咬。这懒孩子,真懒,活该被饿死。”
“妈妈,我想不是那孩子懒。”家华嚼着菜说,眸子里发出一道亮光。
“那是怎么了?”母亲反问道。
“是他妈妈做的那张饼太难吃了。他只咬了一口,就不想再吃了。”
“你这孩子,有这样古怪的想法是不对的。”
“妈妈,你做的饭菜真好吃,我是不会被饿死的。”家华笑着说。
“你真是人小鬼大。我做的饭菜好吃,你就多吃些。”母亲说。
吃过早饭之后,我与家华找二傻拍雪人。
二傻穿着一件薄棉袄,嘴里哈出热气,拿着铁锨又堆了一个大雪人。他将红萝卜塞进雪人脸上当作鼻子,脑袋两边插上鸡毛当作长耳朵。他还把一顶破旧的草帽戴在雪人头上。我们一群孩子围着雪人欢笑。
“雪人只差穿新衣服了。到了晚上,它会溜进我们的屋子里,把我们的棉袄和裤子偷偷取走穿上,它还会骑着自行车去游玩。它也会蹑手蹑脚摸进厨房里,偷吃我们锅里的饭菜。”二傻满面春风,站在雪人前比划着手势说,“走吧,咱们到村头的打麦场上滚雪球、打雪仗。”
我们一群孩子簇拥着他向打麦场奔跑过去,欢声笑语在村庄里飘来荡去。
天色阴沉,寒风呼呼的拉扯着我们的头发与衣服。打麦场上铺满厚厚的白雪,上面留着一串串小动物们的印迹。
一座座麦秸垛犹如雪山耸立在寒风中,一只觅食的老鼠慌慌张张地躲进草垛里,三四只在雪地上溜达的斑鸠展翅飞走了。我们抓起雪用小手捏成小雪球,在雪地上欢呼着互相追逐,互相抛掷。寂静的打麦场一下子沸反盈天。
“嗨,快来瞧,麦秸垛里坐着一个人。”一个小伙伴手里握着一把雪。他诧异地盯着麦秸垛呼喊。
我们一窝蜂地围了过去。只见那座麦秸垛的底部已经被掏空,显然它的主人将那部分麦秸取走使用了,留下的窟窿可以容纳三四个人。我们看到一名流浪女正蜷坐在那里。她大概二十多岁,穿着一件大红棉袄,长得浓眉大眼,头发乱得像是一头飞蓬,脸庞上污渍斑斑,左耳旁长着一颗瘊子。她嘴唇发紫,浑身发抖,一双大眼睛望着我们,一副凄惶与恐惧的神情。
“喂,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二傻走上前问她。
流浪女翻动了一下眼皮,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个村子的?”二傻继续问道。
她坐在那里,手脚发抖,仍然沉默不语,只是转动着眼珠子望着我们。她好像是一只掉进陷阱里的羊羔,望着陷阱外围观的人们,希望得到拯救。
“二傻叔叔,她准是个疯子,或者是哑巴,估计着是昨天晚上下雪的时候她走到这里,雪正下得紧,她就在这里避雪了。”我猜测说。
“嗯,大家谁认识她?”二傻回过头问道。
我们瞅着流浪女左看右看,纷纷摇着头说:“不认识,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亲戚。”
“我看她现在又冷又饿。我们先把她带回村子里烤火,让她吃一碗热饭。”二傻说着走近流浪女向她伸出右手,要拉她起来。“喂,这里太冷了,跟我们回家吧。我们是好人,不会坑你,不会骗你,也不会伤害你。”
她似乎听懂了二傻的话,伸出一只脏手握住他的手,用力起身。她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向村子里走去。她低着头,步履踉跄,身子筛糠似的,走一段路停下来片刻。我猜想她应该是双腿冻僵了,走路不舒服,才走走停停的。
“村头的麦秸垛里发现了一个脏兮兮的女疯子。”孩子们向街巷里喊叫。
大人们纷纷赶过来,上下打量着流浪女。
“大家谁认识她呀?”二傻问村里人。
“她是谁啊?”大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流浪女身上,摇着头说,“不认识,问问她呗,她会说话吗?”
“问了,她死活不开口,像个哑巴。那我先把她带回我家,让她烤火、吃碗热饭。我们不能看着她活活被冻死、被饿死。”
“对啊,你带她回家,先给她弄点儿吃的东西。二傻呀,你老大不小了,村子里你的同龄人生的孩子已经会打酱油了,你还打光棍儿,把她带回家做媳妇生孩子吧。我看她年龄不大,长得也不丑。”薛大攀笑着说。
“二傻,娶她当媳妇儿吧!”我们一群孩子嬉笑着,呼应着薛大攀的话。
“呸,你们这些小坏蛋,都滚开!还是救人要紧。”二傻脸上露出愠色。
他说着带着流浪女向他家走去。流浪女像是一只温顺的绵羊跟着他。
赵奶奶屋子里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响着。她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做着棉鞋。
我们簇拥着二傻和流浪女走进院子,她听到喧闹声赶忙放下手中的针线。她看到流浪女后脸上露出悲悯的表情,赶紧拿起火盆生火让流浪女取暖。
流浪女坐在火盆前的木凳子上烤火,她的身子渐渐平稳了,脸庞上泛出一丝红晕。
赵奶奶在厨房忙着切菜、擀面条。我们三四个孩子坐在灶台前帮她烧火。我们一边向乌黑的灶膛里添加柴禾,一边哐当哐当的拉着木风箱。
不久,赵奶奶端出一大瓷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递给流浪女,饭碗最上面放着一个荷包蛋,一股浓香在寒气里飘散。
“姑娘,面条很香,你快些吃。锅里还有一大碗,你吃完我再给你盛。”赵奶奶和蔼地说。
流浪女接过瓷碗,拿起筷子吃了起来,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好像几十年未曾吃饭似的。
“唉,可怜的孩子,饿成这样子了,阿弥陀佛!”赵奶奶望着流浪女说。
“赵大娘,这碗面条里的香油可真多啊,整个院子都能闻得到香味儿。正好二傻是个光棍儿,这姑娘可以做你儿媳妇了。以后你也不用再为二傻的婚事发愁了。难怪今天一大早两只喜鹊在村头的大椿树上叫来叫去,原来有这件喜事。”薛大攀揶揄说。
“自古姻缘由天定,月老儿自有好安排。我巴不得二傻娶上媳妇,我早日抱上孙子,不过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扭的瓜不甜,还需要人家的父母同意。”赵奶奶的嘴角挂着微笑。
流浪女吃了两碗面条,嘿喽一声打了个饱嗝。我们望着她哗笑。她瞟了我们一眼,继续坐在火盆前烤火。赵奶奶在厨房里烧了一锅热水,准备让她梳洗一番。
二傻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大家在门口踮着脚、伸着脖子看着流浪女。只见她静静地坐在火盆前,时而抬起头瞅着我们。
“你吃饱喝足了,我现在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子的?”二傻问道。
她抬头向他望了一眼,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羞涩。她仍然一语不发。
“二傻,估计着她不是附近村庄的人,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也没人认识她。我看,你们暂时收留她,等她家人来寻找的时候再送她回去。”王守道吸着烟说。
“二傻,娶她做媳妇吧。你也三十岁出头了,该找个女人了。今天你俩就拜天地,晚上进洞房。”有一个村民调侃说。
二傻鼻子里哼了一声,走进屋子里拿了一些东西,头上戴上一顶厚厚的棉帽,扣上军大衣的扣子,然后推起自行车便要走。
“二傻,天这么冷,你这是要干什么去?”赵奶奶追着他问道。
“妈,我要去尉氏县城。”
“去尉氏县城干什么?路那么远,冰雪还没有化,路很滑,很危险。天晴了你再去也不迟。”赵奶奶劝阻说。
“妈,我从县城回来后再给你说。”他执意要去,硬着头皮推着自行车出了院子。
“二傻这么猴急,急着去县城买喜酒喜糖,再给新娘买两件新衣服穿。二傻急着拜天地、进洞房呢!”薛大攀戏谑说。
阴云把天空渲染成了一幅水墨画,晦暗而冰冷。一阵寒风刮来,站在院子里的村民打了个寒噤,缩了缩脖子,嘴里吐出一团白气。
二傻出了门口骑上自行车。他弓着腰两只脚踩着脚蹬,使劲儿蹬着,飞快地蹬到了街口。人们望着他远去的身影,都以为他去县城置办结婚的东西了,想着他会带着喜酒喜糖,带着酒菜满载而归。
流浪女静坐在火盆前,望着村民们的笑脸闪动着清澈晶亮的眼眸。
赵奶奶将一盆热水端到她面前,递给她一条毛巾与一块肥皂说:“姑娘,梳洗一下,洗洗手,洗洗脸,再洗洗头发,变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她将两手伸进水盆里,水盆映照出她的脸庞。她用手指轻轻拨动着水盆里晃动的影子,嘴角绽放出一丝傻笑,然后用手心盛着水,哗哗啦啦的洗了起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节目,节目中间插播了一条寻亲启事,只见电视屏幕上出现一片蓝底白字,播音员铿锵有力地说:“今日早晨八点,在尉氏县水坡镇芦湾村打麦场上发现一名流浪女。该女二十岁左右,披散头发,浓眉大眼,左耳朵边有一颗瘊子,身穿大红棉袄与黑色棉鞋。现寻找其亲人,若有线索,请与芦湾村村民赵德斌联系……”
那条寻人启事比神河粮液的广告还要长。我们一家人停下筷子盯着电视屏幕。
“嘿,赵德斌是二傻叔叔的学名。他上电视啦!”我嚷着。
“我还等着吃他的喜糖,看来他没有去买喜糖。”家华失望地说。
“这么冷的天,他蹬着自行车沿着雪路跑到县城,自掏腰包到县城的电视台给那个流浪女做了一条寻亲启事。他真是个大好人,是个活雷锋。你们兄妹俩长大后要好好向他学习,做个好人,要助人为乐。”母亲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
“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做到人人满意难上加难,做事不损人利己,做到问心无愧就行。”父亲随口慨叹说。
“你不要总是给孩子灌输这些不良思想,拖我的后腿。”母亲瞪了父亲一眼,责备他说。
二傻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村子里有电视的人家大多看到了那条寻亲启事,在街头巷尾谈论着这件事情。
村民们对二傻交口称赞,看到他骑着自行车两手空空回来笑着说:“呵,咱们村的活雷锋回来了,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二傻喘着粗气,黝黑的脸膛上堆满憨笑,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他的那顶棉帽歪戴在头上,毡绒护耳耷拉在耳朵上。他的裤腿上沾满肮脏的泥渍,应该是骑车时溅上去的。
“看你累成狗熊了,还没有吃午饭吗?”王守道嘴里叼着烟卷说。
“嗯,我还没吃午饭,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本想在县城东关塔旁边买个烧饼吃,伸手一掏口袋,发现口袋里没剩下一分钱,就饿着肚子回来了。”二傻笑着说。
“你准是饿坏了,赶紧回家吃饭去。”王守道的笑脸转向我们这群孩子说,“孩子们,我教你们几句顺口溜,你们跟着我学。”
“好呀!”我们一群孩子齐声喊道。
王守道噙着烟卷低头沉吟片刻,抬起交织着笑纹的老脸说:“孩子们,跟着我喊——活雷锋,戴棉帽。赵德斌,心肠好。帮助人,真骄傲!”
我们追着二傻嬉笑,扯着嗓子喊着顺口溜。
傍晚的时候阴云消散,天色暗淡,乌鸦在树枝上嘎嘎叫着。寒风在街巷里吹来吹去,像是野兽在村子里奔跑呼号。
一辆拖拉机挂着车斗载着五六个人驶进村子里,开拖拉机的中老年男人向一户村民打听说:“老乡,这里可是芦湾村么?赵德斌家可住在这里?”
“嗯,你们是不是在电视上看了寻亲启事来找他的?”
“是啊。”
“嗯,我带你们去他家。我们都管他叫二傻。”
“好的,谢谢老乡!”
“走,跟着我向前走,再往左拐就到了。”
原来流浪女的名字叫张秀娟,家在尉氏县城南部蔡庄镇的一个村子里。她十二岁的时候突患一场高烧,高烧退去之后就变得头脑不清,疯疯傻傻了。医生说她患了神经病,好转的可能性极小。两天前她的家人去一个亲戚家参加一场婚礼留她一个人在家,她就离家出走了。她的父母东找西找,急得团团转,谁知道她竟然徒步一百多里路来到了芦湾!
秀娟坐在火盆前烤火,看到她的家人来了抬头瞧瞧,似乎眼前站着的是陌生人。她继续低着头烤火。
她的父母见她梳洗得干干净净,没有挨冻受饿,对二傻与赵奶奶千恩万谢。
“德斌,谢谢你。你真是个大好人。”秀娟的父亲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放在桌子上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这钱你要收下。你到电视台做了寻亲启事,应该也花了不少钱。这钱你收着!你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会至死不忘的。”
二傻拒不接收,说:“这钱我是不能要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经过几次推让,秀娟的父亲只好把钞票塞回自己的口袋里。
秀娟的母亲搂着女儿,红着眼睛哭着说道:“我的傻闺女,我还以为你走失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闺女,跟我们回家吧!”
“这里不就是我的家吗?”秀娟竟然开口说话了。
“傻孩子,这里不是你的家,离咱们家还很远。咱们家在县城南,这里在县城北。”
“我只想呆在这里,不想走了。”秀娟语气坚定。
“傻闺女,那不行,跟我们走吧。”
秀娟死活不肯走,最后她的家人将她五花大绑抬到了拖拉机的车斗里。她挣扎着身子高喊:“这里就是我的家,我不想走,我不想走啦!”她的家人死死按着她的身子,不让她动弹。
“大叔,二傻现在还是光棍儿,让你女儿嫁给他,那该多好啊。”薛大攀向秀娟的父亲笑着说。
“唉,再等等吧,我们一家人需要商量。”秀娟的父亲脸上露出苦笑,转身向二傻与赵奶奶道别,又打量了二傻一番,然后开着拖拉机走了。
我们站在街口目送他们远去。拖拉机行驶了很远,仍然能够听到秀娟高喊着:“我不想走,不想走啦!”
天色越来越暗,苍茫的暮色渐渐覆盖了整个村庄。村庄里亮起一盏盏灯光,驱散一方黑暗,像是夜晚绽放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