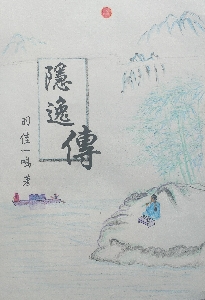故关巡检司设在陇州城西北四十里的陇关,也是汉代著名的大震关,因为唐代在不远设立安戍关而成为故关。虽说关卡在陇山山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并不是除了西北风什么都没有,生活也不是特别单调。
拿九品巡检杨有信来说,除了当值时间没有酒喝也没有人打情骂俏,其他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甚至中午吃饭还能玩几把筛子。就算有点无趣,可比起从过路商贩那里榨的油水也算不上什么。
当然,昨天是个例外,因为他爹打小教他不要跟女人一般见识,更别说那四个女人三个拿着家伙。其实,他当时的做法也不算太过分,有几个男人见到漂亮女人不想多看几眼?而他作为这里的头儿除了看仅多摸了一把,准确说他还没有摸到,就被那小妞斩掉四根手指,还是他用来掷色子摸花花牌的右手。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隐隐作痛,看看午时将近,他打算吃点凉饭睡一会儿,晚上还约了牌局。
一阵马蹄混合和銮铃声,打乱杨有信的计划,他不由得踮起脚尖看,凭烟尘大小他觉得又有油水可拿。转眼间他看清楚来的是个马队,连连向属下摆手让他们打开关卡,他已经认出来这伙人的衣服——镇抚司缇骑。等再看清楚些,他不得不连连摆手让大家下跪,因为领头的是位副千户。
马队接近关卡放慢并在杨有信跟前停住,他头都不敢抬大声唱喏:“故关巡检杨有信恭迎千户大人,恭迎诸位大人!”
“哎,看清楚再叫,是副千户。”说话的就是那位副千户,杨有信赶忙连连称是。副千户又说了:“你就是这儿的头头儿?起来说话吧。”
杨有信赶忙起来,不敢站直腰又得仰脸赔笑,还没有说话副千户又问:“最近过关的有没有个长得富态的老人家?身边还带着家眷。”
未免说错话,杨有信刻意模棱两可的说:“回大人,此处每日过关者络绎不绝,拖家带口的也常有,像大人这般富态的倒不常见。”
副千户听完不由得皱起眉头,旁边另一人说话了:“仔细想想,其中有个拿长剑的,有四尺往上,三十来岁,个头挺高。”
“拿剑的倒是常见到,昨日还有四名女子,三个都拿剑。”杨有信刚说完“啪”的一声,被打了个响亮的耳光。接着有把明晃晃的朴刀伸过来,还是这个严厉的说:“问你什么回答什么,不要废话。”
“是是是,小的最近所见都是普通刀剑,四尺长的从未见过。”杨有信吓得面如土灰。
“你的手怎么回事?”副千户问。
“回副千户大人,昨日有四名女子由此闯关,小的尽量拦未能拦住。”杨有信可不敢说摸女人屁股未遂。
“哦?”那人思索着问,“四名女子?她们做何装扮?”
“回这位大人,一女子着灰衫灰裙,其他女子着素衫素裙。个个貌美如花,言语颇为冷淡。”杨有信头都不敢抬。
“其中可有个绝美绝冷的?出剑奇快无比。”说话的还是那人。
“大人所言丝毫不差。”杨有信不由得看看包扎后渗出血的右手。
“难道是她?”副千户纳闷的说。
“极可能。”那人说着提缰绳调转马头,大声说,“走,先进城与大人汇合。”
话音未落“啪”的抖个响鞭,那匹马仰头嘶叫一声,“哒哒哒”顺官道向山下飞奔。接着又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加銮铃声,留下一阵黄烟。
陇州城面积不大,且西北两面环山东南又临着两条河,繁华地段就是西门内街和南门内外大街。悦君楼酒家就在两条内大街交叉口西南拐角,临街的两层六间是饭馆,后院是客房。既不是城内唯一的酒家,也不是最好客栈,人流量却是最大的。原因自然离不开专业大厨的好手艺,掌柜的姬十二和善的性格与童叟无欺的平民化管理也是重要原因。
酉时初刻,还不到上客点。饭馆只有一桌客人,也是后面卯字房的四位女客,要三个菜一窝汤,刚上一个菜,没有开始吃。随着一阵凌乱的马蹄与銮铃声戛然而止,门口多了二十多匹高头大马,一些戴范阳帽穿官府的人停在门口。有个青年校尉进来订房,说他们有二十六人,要把所有客房包了。姬十二赶忙陪笑着解释,说后面总共只有十二间客房,其中六间已经住有客人;如果他们不介意,倒是有两间大铺房空着,可以给士兵们住,另外一间天字号头房、一间地字号上房、两间人字号梢房可以给长官住。校尉出去少倾又回来,身边多了个穿试百户军装的,说他们可以不包,但除了大铺房必须再给他们六间上房。姬十二再次赔笑说那样不合适,建议他们住南门口的何记客栈,那里有三十间客房,还有宽敞的马厩。试百户立马发起脾气,威胁他腾不出房间就封他的店。
姬十二实在不敢招惹这帮人,就过去跟四位女客商量,那怕多减些房钱请她们换梢房。其中一位年轻女客不仅不肯换房间,还大声说让他把门口的恶狗轰走,免得吠声影响她们食欲。姬十二又被吓一跳,赶忙让她小声,试百户已经听到并瞪着眼走过来。“哪个不长眼的敢辱骂官爷?信不信二爷将你就地处决?”试百户不仅脾气大嗓门也大,说着话已经将左手按在腰刀柄上。姬十二猛然发现这位没有右手,撩袍子的时候也露出刻有“北镇抚司”的牌子,吓得慌忙赔笑打哈哈。
“二爷且慢。”伴随着这声惊呼,刚才那位校尉猛地窜到试百户前面,边使眼色边往外推试百户,同时嘴巴也在做口型。两人退到柜台跟前,险些与闻声进来的几个人撞到一起。试百户脸色煞白地扶住另一个试百户,慌乱地小声嘟囔:“绝,绝,绝,绝尘,绝尘居,绝尘居的,小,小妮子。”
那人诧异的“哦?”一声,又扭头看看四位女客,凑到一位老者耳边小声嘀咕几句。老者的神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分开众人走到离女客桌子五尺左右停住,拱起手边打量边温和地说:“敢问几位与绝尘居士是何关系?”
靠外边坐背对老者的女子站起来,缓缓转身并抱拳轻声说:“居士乃是家师,请问阁下有何见教?”
“哦,失敬了。”老者的手没有往下落,边客气边用小眼睛在对方脸上搜索着,“区区姓何,久仰居士大名,几欲拜望奈何琐事缠身,始终与居士缘悭一面。”女子的年龄约有三十五六,身形轻盈娇俏,穿一身得体浅灰直裰素罗裙,冷峻的脸颊白皙中透着些许红润,嘴角斜上方有两个极难发现的梨涡。
“小女子代家师愧领阁下盛情,只是家师素来不见客,阁下有话不妨直言。”灰衣女人温和又平淡的说。
“原来如此。”老者说着扭头看一眼后面的同伴,“或是区区对属下疏于管教,数月前他们曾与贵派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烦请姑娘代为向令师致歉。”
“致歉倒也不必,只希望他们真是无心之失,不要再肆意滋扰鄙派便可。”灰衣女人似乎猜到老者的意图,“绝尘居素来不与外界交往,也不希望被外界滋扰。”
“哦?不知他们之前冀北双狼是如何滋扰贵派?年初的花狐程见喜与大环刀许亮是如何滋扰贵派?可否请姑娘明示?”老者连连发问。
灰衣女人旁边的年轻女子站了起来,先冲灰衣女人微微躬身小声说句什么,才转向老者说:“明知自己疏于管教,还要阴阳怪气对他人问东问西,当真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这么说小姑娘见过他们?”老者眼中现出几丝难以察觉的欣然,“他们可有冒犯姑娘?”
“少在这惺惺作态!难保他们不是上行下效,仗着有人撑腰恣意妄为。”年轻女子冷冷的说。
“大人面前休得放肆!信不信把你们统统抓起来?”柜台旁边一个校尉大声喊叫。
“信,你们方才不是还要封人家店?现在逞威风欺压良善也不为过。”年轻女子迅速接话,又看着老者说,“你们的朝廷养你们不就是为了这个?”
“好凌厉的嘴!不知姑娘的剑法是否同样凌厉?”老者说完退后一步握住剑柄,是一个光秃秃没有剑穗的剑,剑柄顶端是个一寸半大小的镂空圆球。
“一试便知。”年轻女子说着就把腰间的剑带鞘摘下来,横着摆在胸前,剑柄上一条两尺多长带有银锁扣的蓝灰色剑穗微微晃动。
看到年轻女子拿剑,柜台跟前几个人都瞬间紧张起来,门口的校尉也纷纷拿起武器。姬十二吓坏了,赶忙满脸赔笑劝大家,紧着说好话却又不敢靠他们太近。桌子跟前另两个女客倒是不以为然,站起来观察众人并没有阻止的意思。
“掌柜的,麻烦给我来几个素菜,一碗白饭。”随着一句清脆甜润的声音,有个紫衫素裙的女人从楼梯旁的后门出来。看到厅里的形势即刻停住,语气里反而带着挑衅:“哟!这是要干仗啊?那算了,我还是回房吃吧。掌柜的,麻烦你把饭菜做好拿到天字酉号。”
大家的目光不由得转到紫衫女人身上,看起来有三十七八岁,身高五尺五寸,发际线偏高,微黄稀疏的头发中零零散散带几根银丝,脸颊清瘦颧骨略凸,似笑似不笑的眉梢带着几分媚味,大眼睛炯炯有神,腰间明显盘着一把镶玉软剑。姬十二先尴尬地笑了笑,凑近两步才低声说忙完手头事情马上安排,还刻意向身后瞄一眼,并指着后门让女人回房稍候。
“罢了,还是不影响旁人用饭的好。”老者松开剑柄,紧绷的表情瞬间转换为和颜悦色,看着年轻女子温和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区区改日再领教姑娘高招。”说完退后几步,摆手示意大家收起家什。
年轻女子仍然单手拿剑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老者腰间的宝剑。灰衣女人看着紫衫女人转身出后门,才收回眼神轻轻冲几人摆手说:“坐下吃饭,不要与无谓的人做无谓争执。”说完坐下来继续吃饭。
姬十二看双方的火气都收住了,赶忙笑着过去招呼老者往楼上走。旁边的试百户和校尉们纷纷跟上来,边走还纷纷看着几位女客。姬十二走上楼梯又停住,吩咐伙计不要再招揽住客,把官爷的马牵后院饮水喂饲料,完事紧跑几步向他们介绍本店的拿手菜。
晚霞褪尽凸月初明,城南一里的千河畔清风微漾,涓流潺潺。
小河转弯处的北岸有一个长满矮树的小土岗,土岗坡下距小河十多步并排站两个身影,凭婀娜的身姿和随风轻摆的裙角,可以分辨出是两位女子。右边略高的女子似乎刚刚哭过,边用手绢擦脸边说:“真希望当初死的是我,你们堂姐妹还能团聚。”
“你不必这样说,人活着就该往前看。”稍微低点的女子声音细腻,停顿一下往河边走了几步,仰脸看着天空说,“或许那就是新燕的命。”
“不,那不是新燕的命,是老毒妇剥夺了新燕的命。”高点的女子执拗的说。
低点的女子回头看着同伴说:“轻歌,不要这样行吗?事情都过去快二十年了。”
“不要再叫我轻歌!叫我春梅!”高点的女子显得有些激动,“这个仇,到死我都不会忘!你可以不在乎新燕这个堂姐!我不会不在乎我最好的姊妹!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后面的话几乎都是喊出来的,喊完又擦擦眼泪,缓和些说,“你知道吗?离开绝尘居那天我对天发过毒誓,只要我邓春梅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放过老毒妇。说真的,好多次我都希望老毒妇那天刺死我,我就可以和新燕在一起,我就不用承受旧伤复发时那种钻心疼痛。”
“春梅,你——”低点的女子心里也一阵难受,几步走到邓春梅跟前温和的看着她说,“仇恨是把双刃剑,伤害仇人之前早把自己割的遍体鳞伤,值得吗?你到底跟她有仇还是跟自己有仇?”
“我不在乎!”邓春梅坚定地说,“宁可粉身碎骨我也要报这个仇,哪怕跟老毒妇同归于尽我也甘心情愿!”
“你——你也太——”
“你刚才不是说命吗?这就是我的命,从我和新燕偷进后堂那天就注定了,命运把我们俩栓到一起了!如果那天死的是我,我相信新燕也会为我报仇。”邓春梅的情绪已经稳下来,使她平稳的不是安抚,而是陪伴她近二十年的仇恨。
“唉!真不知道还能怎么劝你。”低点的女子叹口气又扭头看向河水。
“你就不该劝我。”邓春梅反过来凑近低点的女子,“我知道你打小心肠软,所以不图你与我里应外合,你若有心就盼我早日成功吧,新燕泉下有知也会感激你的。”
“我觉得有件事可以帮你。”低点的女子转回身认真看着邓春梅,“记得我方才说那个人吗?他精通岐黄之术,保不准他能治好你的旧伤。”
“死我都不怕,这点伤又能把我怎么样?”邓春梅不以为然说。
“春梅,生命的意义远不止于复仇。就算为复仇,万一关键时刻旧伤复发怎么办?去除旧伤不是可以全身心投入复仇?”
“有这个可能吗?”邓春梅有些动摇。
“有。”低点的女子说,“你要对他有信心,也要对你自己有信心。”
“那就尽管一试吧。”邓春梅的语气逐渐温和下来,“就算不行也不打紧,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
“要有信心,态度要积极,要乐观。嗯?放心吧,我相信他一定能治好你的。”低点的女子信心满满。
“嗯。”邓春梅点头,“我明天跟你一起走。”稍微停顿又说,“分坛的人说,那些人前阵子在凤翔府城和麟游县出现过,教主家女娃儿也是在凤翔府城附近失踪的。”
“那咱先去西安府落脚。”低点的女子说。
“什么?”邓春梅不解地问。
“暂时还不能让她们和他见面,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低点的女子看着邓春梅说,“就说分头寻找,让她们在西安府寻找,咱两个去凤翔府。”
“这也行。”邓春梅点头。
“走吧?太晚了她们可能会起疑。”低点的女子说。
“行。”邓春梅答应过又淡淡的摇头,“还是分开走好点,明日早饭时再假装认出来。”
“那我先走一步。”低点的女子轻声说完就要走。
“嗯。”邓春梅又点头,忽然又说,“最好不要与镇抚司那些人动手,尤其领头那个鬼使何易,你们还不是他的对手。”
“明白,走了。”低点的女子说完快速上土岗,两三丈后开始施展轻功,快速消失在城墙根。
邓春梅没有上土岗,而是慢悠悠的顺着河边向西漫步,接近城南官道才走上来。路上的行人逐渐多了,还有马车,还有推独轮车、挑担的,趁月光赶路的人真不少。
南门外最醒目的要属一串四个红灯笼,高高悬挂在城门外五十多步的桅杆上,红底黑字写着“何记客栈”四个字。
二更梆子声响过,一个黑影从城墙上飘落,在桅杆顶端一点,画弧形贴在屋檐内侧的廊下立柱。看清楚天字丙号房在二楼东南角位置,轻推立柱斜着滑过去,正落在丙字号门口,抬手轻轻的叩了一长两短三下。门“嗞”开了条一尺半的缝隙,随即传出个清脆甜润的女人声音:“进自家店跟做贼似的,你这从四品命官做也的太没意思了吧?”
黑影侧身进房,轻轻关上房门穿过门栓才温和地说:“凡事谨慎些无大错。当今的主子喜怒无常且不形于色,加上缉事厂的阉狗横行无忌,朝堂又有那些红袍老儿处处刁难,我处于这种不上不下的位置尤要谨慎。”听声音是个男人,脚步停在离门九尺左右。
“咯咯,”女人轻盈一笑接话说,“那你怪谁呀?当初你若不贪恋这身蓝皮,留在巴州守着二亩薄田一洼茨菰,如今也活的悠哉悠哉。”
“若不是有这身蓝皮,你梅大护法会看上我?”男人说着忽然压低声音笑着说,“恐怕至今仍旧是个不知枕席之乐的憨批老汉儿。”后半句带着浓郁的川北音。
随着一阵窸窸窣窣宽衣解带,木床也发出吱吱声,女人忽然又说:“等一下。”
“嗯?”男人的声音明显有些不悦。
“我天亮就得走,还要从账房支些银子。”女人柔声说。
“半年多未见,刚见又走?”男人的不满迅速膨胀,“凌老鬼招你了?这么远迟个一半天也无妨,再留一天。”
“不是,傍晚时我与老毒妇的弟子相认了,她要带我见个人,说什么能治我内伤。”女人说,“老毛病了,治不治倒也无关紧要,我反而想趁这个机会——”
“哎——”男人打断女人的话,“有机会治当然要治,我还想着那天混不下去就告老还乡,你我一起种个菜钓个鱼。你若无旧疾缠身岂不更好?”
“嗯,若真有那一天我虽死无憾。”女人说。
“当然会有,首先不要丧气。去吧,好好把病治好。你明早多支些银子,别害怕花银子,你我无儿无女,银子除了花给你还有何用?”男人越说越感触。
“其实我更想趁这次机会把剑谱弄到手,万一将来撕破脸,咱也不用顾忌老毒妇。”女人又说。
“剑谱?你说惊鸿剑?那东西她不是随身携带吗?”男人的语气有几分诧异。
“听说老毒妇把它传给一个叫惠香的女娃儿,就是傍晚当你面拿剑那个女娃儿,得亏你们没动手。”女人意味深长的说。
“有这种事?难不成要定这女娃儿接掌绝尘居?”
“按她的说法不是,好像为追杀什么人。”
“哦?这倒新鲜。”男人稍微停顿又压低声音说,“你不妨弄清楚杀哪个,从中使个——嘿嘿嘿,么得永远的朋友,也么得永远的敌人。”
“我尽量试试。”女人答应。
“莫要再说别人的破事情,明日一别还不知道多久才能见面。”男人说完这话“噗”将灯吹熄。
屋内的平静仅维持片刻,木床又“吱吱吱”响起来,还有细小的娇吁……
卯时末,陇州当地人才开始吃早饭,醪糟汤、臊子汤饼、牛羹煮饼、油楦子、面茶、钱钱肉,每个都带着浓郁的西北特有味道。悦君楼酒家处于早市中间位置,几种小吃也做的像模像样,价格和街边摊相同,就餐环境却干净优雅,还有清茶免费供应。所以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在门口台阶上蹲着吃的也大有人在。
一楼靠窗位置的四位女客早已经吃过了,仍稳稳地坐在那品特制香茶——姬十二从镇江府带的茅山青茶加菊花,欣赏着屋里屋外不一样的民俗风情。忽然,一个穿紫衫素裙的女人停在她们桌边,欣喜地看着穿浅灰直裰素罗裙的女人说:“你,你是不是李家新月妹妹?”
灰衣女人站了起来,也满脸惊讶的打量对方,语气也显得很惊讶:“我已经不姓李很多年,你是什么人?怎么知道我?”同桌的三位素衫素裙女子都抬头看着她们,脸上满是惊讶。
“呀!真的是你?”紫衫女人更激动,“我是春梅,邓春梅,你忘了?咱们两个村就隔一条水沟。”
“哦——我想起来了,那时候你常常到沟这边来玩耍。”灰衣女人脸上现出甜甜的笑,嘴角旁边两个梨涡分外美丽,“快三十年不见了吧?你真没有一点小时候的样子,不是你叫我,我绝对不敢认你。”
“是呀,一晃这么多年了,我们都老了。”紫衫女人说着一指身后,“我就在后面,咱两个到我房间聊好吗?”说完可能觉得冒失又做补救,“几位妹妹和你一起的?都到我房间坐吧,我让伙计重新沏茶。这下好了,我正愁一个人孤苦伶仃。”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个都是我同门晚辈。”灰衣女人随即指着对面左侧女子,“这是我二师姐的弟子,叫荷香。”手指轻移指向对面右侧女子,“这是我四师姐的弟子,叫香菱。”说着又拍拍身边靠窗女子的肩膀,“这是我的三弟子,叫惠香。”
话音未落,惠香站起来冲邓春梅躬身抱拳一揖说:“惠香见过邓前辈。”对面的荷香和香菱见惠香施礼也匆忙抱拳躬身说:“荷香见过前辈。”“香菱见过邓前辈。”
“咯咯咯咯。”邓春梅先报以清脆甜润的笑声,才亲昵的打招呼:“你们长得个顶个漂亮,我非常喜欢。走,跟我回房,咱们好好聊聊。”说着优雅地转身往柜台走,老远就冲姬十二喊话:“掌柜的,麻烦给酉号房沏壶最好的花茶,再来盘新鲜果子,还要糕点,我招待失散多年的亲姊妹。还要让你家小伙计帮忙跑个腿……”
灰衣女人刚走几步,后面的香菱过来轻声说:“玉颜师叔,清规规定不能与外人结交,你怎么可以——”
“这里不是山上,而且咱们还有事情要办,怎么可以墨守成规?”玉颜停住压低声音说,“咱这几个月是不曾与任何外人交往过,可事情同样毫无进展。如果春梅对关西道熟悉呢?是不是凑巧能帮助我们?是不是可以少走点冤枉路?再说,咱的盘缠还有多少?是不是要等分文皆无了再想办法?还是你打算沿路乞讨回招隐峰?”见香菱无言以对又看荷香,“你怎么看?”
“荷香无异议,一切听凭师叔做主。”荷香从记事到现在二十七岁,可以说连山都没有下过,毫无出门经验,听到乞讨回招隐峰都吓住了,见问她就赶忙乖乖的回话。而下山近两个月来她也是以“盯”为主,几乎不发表意见,下山前她师父交代的任务也仅仅是“盯紧玉颜师徒”。
香菱见荷香附和也瞬间慌乱了,她虽想在师父师祖面前表现,但也不敢冒太大险,真要被她们孤立再找机会甩掉她,别说沿路乞讨,她都怀疑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回得去绝尘居。所以荷香话音未落她就接着附和:“香菱听凭师叔做主。”
玉颜淡淡的“嗯”一声,随即温和的说:“出门在外一定要心齐,不仅有利办事情,别的门派看我们同声共气也不敢小觑。”
“是。”“师叔教训的是。”荷香和香菱迅速回话。玉颜说完转身
往后院走,她们快步跟在她身后。
惠香没有发表看法,也不需要,无论在山上还是下山后,她始终对玉颜满怀敬意和感激,对师父的言行从不质疑,就算有也只是诧异,而且让她对师父越来越心悦诚服。
就拿下山前一天来说,按师祖的意思她们收拾好东西就要立刻出发,即使要去的方向也没有,因为师祖的脸色铁青,肯定在生气。她清晰记得那是申时初,从竹林回山后又困又累,别说早饭,连水都没有喝一口,简单收拾几件衣服进后堂拜别。师祖再次向她们申明任务,并强调不达成目的不准回山。等师祖说完,师父忽然提起竹笛碎片里的几个字,说记得在藏书室哪本书里见到过,还说正确排列几个字或许能找点那些人的踪迹。于是,所有人到清圍前面翻书,把带有山、篱、西、青、关、黑的书籍都找出来。直到太阳落山,总算在《太平寰宇记》里找到“关西道”“嘉峪关黑山”“辽阳黑山”三个东西相差好几千里的地名。大家都诧异这天南海北的有什么关联,师父却借来兰香的柳叶刀在地上画个六边形,又把对角连接分别写上“关西”“黑山”“青篱”。师祖当即大声说:“好!玉颜,你们明日出发,这个叫青篱的或许真在关西道一个叫黑山的地方。”随即吩咐厨房备饭,让竹棋给她们拿盘缠。那一刻她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所有弟子都把羡慕的眼光投在玉颜脸上,她似乎也能感受到那股荣耀。
下山这五十多天,惠香又见识师父的沉稳干练。沿路晓行夜宿、谨言慎行,遇事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对外面的新鲜事物既不好奇也不排斥,根本不像在绝尘居与世隔绝二十多年的人。出潼关就是关西道,这近一个月她们走遍同州五县、华州五县、西安府城、乾州三县、耀州四县、邠州及辖下淳化县,凤翔府七县一州也即将结束。本来昨天打算出陇关的,奈何问路时被关卡的巡检骚扰,她气急把那人手指斩断。师父说肃杀之气使人烦躁,决定回来休息半天今天出发,却又遇到故人。说老实话,什么时间走、走不走她都无所谓,内心甚至希望永远不要找到小蝶他们,她也知道不可能,因为不出半个月她们的盘缠就会用完,无论谁回去取都势必被师祖训斥,说不定还会给出最后限期。
邓春梅真的非常热情,除了好茶点好招待,还给三位晚辈分别送了包括挑心、分心、啄针、簪、钗、金丝髻、掩鬓、耳环、领坠、手镯等小十件金镶玉首饰,三人难为情的推脱时,玉颜摆手让她们手下,并让她们称呼她梅姑姑。随后她兴致勃勃的问她们打算去哪里、何时出发,说自己闲着无事可以带她们四下里游览。玉颜谢过又表示不希望麻烦她,但还是把近一个月寻人不遇简略说了一遍,又说打算出关再找。她马上说她们之前可能找的有些粗略,西安府城南边山区还有几个县没有找,而关西道最好隐藏的就是秦岭七十二峪。这样以来她们就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听取她的提议再返回西安府,吃住都由她安排,还答应找熟识地形的人带她们分开找。
位于西安府城东门大街中段路北的何记客栈,前院一楼是饭堂,二楼和三楼是五间官房、两间头房,后院是六间梢房、四间通铺,后门口是马厩。左边隔条胡同是蝎魔寺,右边紧邻武威镖局,正对面是咸宁县衙,县衙的西临是和宝银楼。邓春梅和玉颜几人包下何记客栈两间头房,一间她和玉颜同住,另一间让惠香三人同住。安置好又带她们到和宝银楼购几件新款双铤金钗,她似乎与客栈账房、银楼掌柜、县衙门口的衙役都熟识。
从银楼下来,邓春梅要带他们吃府城最负盛名的伊香楼羊羹煮馍。玉颜说她们习惯清淡饮食,晚饭尤其要吃清淡些,于是决定返回客栈吃点蔬菜粥。刚进门,客栈掌柜何四迎过来,满脸赔笑说:“哎呀,梅姑,您可算回来了,有几位京城来的大爷执意要住三楼头房,您行好给换换?”
“行好没有问题,你让他们住官房好了,房资都记我账上。换房间门儿都没有。”邓春梅说完,招呼玉颜她们在靠门口第二张桌子坐下。见何四还在尴尬地赔笑,摆手说:“给我们来几个清淡小菜,再来一窝蔬菜粥。”
“嘿嘿,梅姑,您帮老何个忙吧,那些人脾气有点大。”何四又凑近恳求。
“哎?我说何四啊,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要是在平时吧,你说咋换我二话不说,可今天是我招待多年不见的好姊妹,你成心是不是?”梅姑没好气的白了何四一眼。
这时候跑堂伙计端着茶壶茶碗过来,何四边招呼倒茶边笑呵呵说好话:“梅姑这话屈枉老何了不是?老何什么时候敢在您跟前放肆?只不过今天——”
何四没有解释完就被邓春梅打断:“行了吧,别唧唧歪歪,我说不换就是不换!去去去,赶紧让后厨备饭菜。又不少你半点银子?”
“银子我们爷也照付,”从柜台旁边走来一个白脸青年,头戴皂色逍遥巾,身穿皂色缎绣直裰,脚上是薄底绒面靴,背后斜背一把皂色油伞。这人边走边从怀里掏出一块三两小金锭,到她们跟前放在邓春梅面前桌子上,“这个送给夫人吧,虽不算多,但打一副簪子应该绰绰有余。”看似平静温和的话,却透着一股盛气逼人的气势。
邓春梅看都不看那人一眼,把金锭往外一推冷冷地说:“好意心领,但我还是不换,我刚才已经说了,房子不是为了我自己住,是为招待多年不见的好姊妹。”
“送出去的东西我从不往回收。”白脸青年说着往金锭上面轻轻摁一下,手移开后再看金锭矮一节,足有三成嵌进桌面。
“你这是——”邓春梅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就要发火被玉颜止住:“没有关系,咱们姊妹又不是娇惯人,头房梢房没有什么区别,嗯?”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那老何这就让人把几位的物什拿到二楼上房。”何四赶忙向玉颜点头哈腰表示感谢。完了想把金锭拿起来给邓春梅,可他拿几次硬是没有拿动,只好再次尴尬地看邓春梅。她冷冷一笑说:“我说过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再要?”说完拿起个没有来及倒茶的茶碗往金锭上一砸,“噗”“啪嗒”,金锭连同一个木块落在桌下方的地板上面,桌面留下个洞。她看也不看一眼,然后又把完好无损的茶碗放在桌上,转身拉着玉颜往楼梯口走去,嘴里淡淡的说:“既然我妹妹同意,那换吧,东西我们自己拿,你待会儿把菜和粥送到房间来。”
“周平,不必给人家添麻烦,你我不过是出来办事情,又不是来享受的。”靠大厅后墙的桌子有位客人站起来,先冲白脸青年摆手,又冲邓春梅几人抱拳,“抱歉啊,我这位兄弟行事鲁莽,冲撞夫人和各位了,在下代兄弟赔罪。其实我们就是找个地方歇脚,住哪里都是一样。”随即冲何四拱手说:“麻烦掌柜的给这几位女客加两道好菜,算是在下赔不是。”说完又扭头看白脸青年,“还不快向夫人告罪?”说完这话又温和地冲邓春梅抱拳,脸上始终带着沉稳的笑容。
被喊做周平的白脸青年立刻转身,恭敬地抱拳躬身一揖说:“方才多有冒犯,请夫人见谅!”刚才那股凌人的气势瞬间消失了。
“不用了,我也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邓春梅轻轻摆手,然后顺楼梯往上走。见周平灰溜溜回到后墙那张桌,不由得扭头多看两眼。说话的那个人刚坐下,是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长得干瘦干瘦,脸色蜡黄,窄额头高额角愈发显得头发稀疏;腮下几绺发黄的短须,稀眉毛大眼睛,眼窝深陷,太阳穴向外鼓着;身穿深灰缎绣襕衫,头戴大方巾,身披皂色袍子。旁边是个面貌白净的年轻人,没有半点胡须,弯弯的眉毛如同在白纸上描画的,表情深沉二目涣散,头戴圆顶三山帽,身穿枣红缎面襕衫,披皂色绒面披风。同桌其他六个人和周平差不多,年龄都在三十以内,都戴着皂色逍遥巾皂色飘带,身上不是皂色缎绣直裰就是皂色绸面襕衫,搭配深色褶袴;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薄底皂色绒面靴。
“哎,那,那位京城的客爷,梅姑啊,你们这是——”何四站在楼梯口左右为难的嚷着,“哎,这房子到底是换不换?”
“换呀,不说过了,我和妹妹这就上去拿行李下来。”邓春梅轻盈的说。
“不劳烦夫人了,我们住上房已经很好了。”干瘦男人几乎同时站起来说,双手抱拳拱起,脸上带着笑。
“那位大爷不必客气,我们虽是女子却也守信,既然我妹妹已经答应又怎能反复呢?换了吧。”邓春梅停在二楼转弯处笑着冲干瘦男人拱拱手。
“岂敢?岂敢?君子不夺人所好。”干瘦男人再次婉拒。
“我们同意便算不得夺了。”邓春梅迅速接住话,“就这样吧,江湖人应该干净利落,君子和女子也无须分的过清。你说是不是?”
“既然夫人这么说,在下便多谢夫人割爱了。”干瘦男人说完又看向何四说,“掌柜的,夫人几位住店期间的所有花销皆由在下来汇。”
“好,好,好,小的这就吩咐——”何四还没有说完,门口多了几个穿衙役衣服的,其中有人冲他打招呼:“老何!生意撩滴很(非常好)嘛?”说话这位年龄在二十七八岁,个头不高,长相憨厚,留八字胡,说一口地道长安话。
何四扭头一看是县衙快班班头杜宏,身后还有五个快班衙役,赶忙拱手往里面让:“哟!杜头儿,几个伙儿都来咧哈?来,往屋坐,我家爷从金华府捎的酒还有,我给几个伙儿打一角试试。”何四是用掺杂长安话的川北话热情招呼。
“喝酒改一天,今个有正寺(事)。”说话的是杜宏,说话间已经跨进门槛,“不知道啊(哪)个狗式地(骂人话)搁连云栈劫咧缉事厂地金子?闹(弄)地哉(咱)伙儿二半夜不得安生!”
“连云栈?那不是归凤县管吗?”何四凑近笑着应和。
“咦!金子!头儿,制达(这里)咋有块金子?”忽然有人指着门口靠窗的桌子下面嚷,随即捡起来给杜宏。
“奏思(就)!制(这)上头也么写字!”杜宏把金块掂了掂,又翻过来翻过去看看马上大叫,“老何,先舍(说)好,伙儿可不是针对你,狗式地闹不好就在你店里!呃(我)说伙儿!快!喊人!封店!”
说话间,几人都把腰里的刀拽出来,先把前门口给堵住。有两个人快速穿过大堂,跑到院子后门,另外有个边往对面县衙跑边喊:“人咧?科利马擦(利索些)出来,乃锤地(骂人话)贼搁对个客栈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