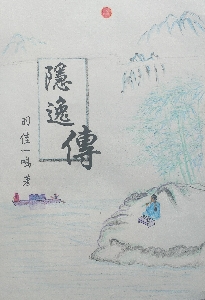新天地广场是贵州G城的中央,用皇冠上的珍珠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风光如画。苟洱早早就备好了相机,她最爱做明信片了,这次她要利用办案的机会做几张,至于送给谁,她没想好,但做好了放在那,她就觉得踏实了,这算不算是一种变裂?苟洱不知道。她已经做了上万张明信片,不过,都是川西和藏东山旮旯里的照片,因为单身的这些年,她只要去川西和藏东,都会拍,她喜欢那里的干净,这和她头脑中的圣洁的爱情不谋而合。这次非拍不可的另一个原因是陈军军、检举揭发的工人都提到了G城中央广场,因此,苟洱要用镜头来佐证这个广场的意义。
离所长约定的吃饭时间还有半小时,苟洱挂了相机到中央广场的喷泉处站了站,发现没什么过人的景色,觉得自己上当了,原来老百姓眼里的审美还真是庸俗,有一两个喷泉就了不得了,直到这时,苟洱才发现自己是个自然主义者,她不喜欢一切违背自然的东西,比如这建筑,她觉得这自然不过的山区大城,就应该是它原本古朴的样子,无论什么生存状态,都是好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人家的语言和习惯,包括吃饭穿衣统统都改变了呢?人家在这里生活得不快活吗?非要关在水泥房子里就快活了?
想到水泥房子,水泥街道,原本充满了氧气的城市,被尾气包围着,她连顺手拍了两张的兴趣都没有了,一个人恙恙地走到了放鸽子的地方,看着飞来飞去的格子发呆。
几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过来抓鸽子,把鸽子惊跑了不少,她想同抓鸽子的孩子说几句,发现小孩子后面跟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女人,面无血色,走路有气无力地,这女人上前两步,拉着小孩子的手就往西头走去,小孩子死活不依,还要抓鸽子玩,那女人使劲朝孩子的屁股上拍了几巴掌,孩子哇哇大哭起来。
苟洱想去制止年轻女人的暴力,但又想,人家管教自己的孩子,自己多什么事呢?便叹了口气,转过身去了。刚转了身,一眼就发现百米远的石蹲立柱那边有个瘦高个子正朝自己这边走来,那人留着一个好生眼熟的西瓜皮头发,苟洱心跳加速起来,她又大眼再睁,瘦高个走得更近了,他的特殊头型——西瓜皮也越来越清晰了!苟洱惊问:这人该不会是三只手吧?
近了,再近了,苟洱每秒钟都在加速辨认,她需要准确的答案。
只差二十来米远了,苟洱最后再问自己:是不是他?答案很快就被苟洱肯定了,那人就是三只手,三只手快速朝年轻女人和小孩子走去。
苟洱不管他走向谁,他是全国通缉犯啊,必须抓的!
“狗渣,看你往哪里跑!”苟洱骂道,手摸到了枪,立即拔了出来,三步两步向三只手疾飞过去。
三只手还在紧步走向那女人和孩子,没注意其他,忽然他发现一个女人朝自己跑来,他仍然没在意,一是因为苟洱是个女的,二来他的反应并没有苟洱奔跑速度快,中枢神经还没有把危机反射出去,但他毕竟是在黑道上混迹的,三只手看到苟洱手里的枪了,他立刻就反应过来了,别的东西对他来说,此刻都是温柔的,可枪这东西,却是夺命天敌。
生死一线、你死我活的时刻突然到来了!
三只手没有选择转身逃跑。
他太知道自己的体力和体能了,此刻如果选择逃跑等于选择立即死去,他象征性地跑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因为他的旁边正好有卖熟食的摊贩。
他一把就将卖马达滚(一种糯米粑粑外面粘了炒熟的黄豆粉的吃食)的老太太从小椅子上拖了出来,拽着她的外套,然后把老太太挡在自己胸前,他的动作简直就像巴东舞蹈,一气呵成,还训练有素。
苟洱本想离他再近一点再开枪,可没想到他会拿人质。苟洱暗自喊苦,但她后悔已经迟了,因为她严重失算。
苟洱只好停止前进,但脚却不甘心,慢慢前移,她想先靠近再寻找机会拿他。苟洱这么明显的意图三只手怎么会让她得逞呢?
不知什么时候起,三只手的手里居然抓了一把小刀,他握刀的方法很特别,是反着握的,掌心在上,刀口那锋利的刃片可以更紧密地贴在老太太的颈动脉处,血管一起一伏的搏动让刀也跟着起伏。老太太似乎感受到血管已经被冰冷的刀刃划开,血流即将成柱,她一声接一声嘶裂、惨叫、挣扎,三只手被她的尖叫声逼得只好把刀用力抵达皮肤、脂肪、肌肉、血管,老太太脖子开始渗出血了,三只手骂道,“再喊,搞死你!”
“你赶紧放下刀,我不会开枪,如果你不照办,我一定会开枪!”苟洱说着就把手抬了抬。
苟洱边说边向三只手靠近,她离三只手越来越近,三只手拽着人,跑不动,他便懒得动了,朝苟洱大喊:“你退回去,一百米!不,两百米!你让我走,否则我开枪打死她!”
什么,他除了刀还有枪?惨了!苟洱听到他说要开枪几乎不敢相信。
但三只手没有使诈,他非常迅速地换了手,等他用左手食指扼住老太太脖子的时候,右手已经掏出了一把枪来。
这种枪,苟洱闭着眼都知道,P12!它和自己的枪一模一样,连颜色都一样!苟洱脑袋快速地打着问号。第一问是这么好的枪都用上了,他还抢他奶奶的烟干嘛?他抢别人不就完了?说不定钱更多,三只手到底什么来路?三只手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新天地广场?难道他在跟踪自己?还是有人泄露了情报?他今天是团伙行为?如果是,目前这个中央广场自己将无法控制了……
放不放?放了,今后抓捕更难,如果不放,今天的情形很难预料,最坏的打算就是死人。苟洱领教过三只手的残忍,他连亲奶奶都杀,还会给谁留活口?苟洱不敢再细想,她必须立即作出判断。
三只手见苟洱不动,朝天开了一枪,苟洱从枪声中惊醒过来,她假装放下枪,三只手并没有撤退的迹象,苟洱在弯腰的当口,把枪口对着三只手的右脸部的位置扣动了扳机,而与此同时,三只手也扣动了扳机,他的子弹直接射进了老太太的头部,老太太一声不吭就倒下了,几乎是同时,三只手也倒下了。
苟洱亲眼看见三只手倒了下去,老太太的身体盖在三只手的身上。苟洱约略放心了,她没有马上去看倒下的两个人,无论是谁,她认为只要中了弹,必死无疑。
很快,苟洱听到尖叫声,她知道,有目击者亲眼目睹了死人一幕。倒戈,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但尖叫声提醒了苟洱,刚才要抓鸽子的孩子和要捉住孩子的女人不能丢了,三只手似乎就是朝她们俩来的。趁着混乱,自己可以把那俩人控制起来,这样,如果真的有幕后,她俩就是非常重要的线索,三只手既然已死,就不能让活线索再中断。
苟洱握着枪,在新天地广场鸽群最密的地方找那女人和孩子,可哪里有踪迹?
此时的广场,人群醒悟过来了,如惊弓之鸟,很快,围观这场枪战的人连出口的缝隙都没有留下。
失去了活线索的苟洱垂头丧气,她要回到现场,准备处理三只手和被他打死的无辜老太太。她刚走两步,就听到一声枪响,紧接着,子弹朝自己飞过来,子弹从苟洱的裤脚边擦过,裤子被打穿了一个洞!
天啊!一定是三只手的同伙出现了。苟洱告诉自己。
可是,围观的群众像群体触电,惊恐万状,魂飞魄散的人群再次向四面八方逃散开去。
苟洱猜错了,并不是三只手的同伙,而是三只手开的枪。
他已经推开老太太的尸体,躺在地上,从围观者的脚缝隙里看到苟洱就在不远处,他要杀了苟洱。
三只手爬了起来,随手又对着逃散的人开了一枪,又有人倒下了。趁着混乱,三只手很快就消失于广场了。
苟洱不敢再乱开枪了,她甚至不能再追击,只能看着他趁乱跑掉。
所长带着人很快赶到,包围了整个广场堵住所有三只手可能出逃的路口,但谁也不敢保证,围堵可以亡羊补牢。
一念之差,苟洱铸成大错。她检查了一下,加上老太太,一共死了4人。
苟洱的枪法没得说,她选择了老太太右耳旁的位置开的枪,这里是三只手蝶骨和颧骨之间的位置,即使脑核伤不着但脑缘系统可以破坏掉,只有伤到了这里,他不可能有活的。但三只手终究还是跑了。接下来,局面就变得尤为复杂了。
不仅是苟洱要疯了,易副局长和钱巍的电话也要疯了,轮番打进来,苟洱越是不接,铃声就越疯狂。
易副局长问:“苟洱,你还好吧?”
苟洱咬着牙,她快要把嘴皮子咬成纸一般薄了。
“余谈一定会绳之于法的,你也不要自责了。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没留下活口。”
不说“余谈”,苟洱几乎忘了三只手的大名,苟洱这才知道,易副局长还不知道三只手
已经跑了,他以为自己打了个不胜不败的仗。“易副局长,您错了,我留足了活口,可是,那是用四条命换来的活口。我真没脸见您。” 苟洱几乎要哭出声来。
“别自责,也许换了别人还不如你办得漂亮呢,我们低估了三只手和他后面的人。”易副局长还算是懂得领导艺术工作的人。
“老太太好好的,就这样没了,我真他妈的没用,要早出手就好了,我太犹豫了,真的,要是一开始就打他的手或腿,老太太就不会白送命了!……我才是杀人犯……要是我不去找那被拐的女人还孩子,我就不让后面的人也死在我手里,顶多就是我自己赔上一条命!”苟洱想不流泪的,但她想到那直挺挺的尸体,她就没法控制情感。那是命,不应该那么早死的命。
“这样吧,抓捕的事我还会和罗坪那边沟通,你就不要管了。我这次派给你的任务还是要完成,不要,咱们也不能全军覆灭啊!失利的事哪里没有?长征路上,毛主席不都吃了很多败仗吗?你调整一下情绪,继续办案啊。”
易副局长的话让苟洱听着很舒服。她轻轻的“哦”了一声,算是调整完情绪了,钱巍的电话来得还算是时候,至少在表面上,苟洱好过一些。
钱巍并不知道罗坪这边发生的一切事,他只知道苟洱跑监狱的事,不知为什么,他就是特别担心苟洱这一趟出行,在易副局长之前,他已经狂打了三四十次电话了,苟洱手机静音了,苟洱越没接电话,他越着急,他不缺联想,苟洱死了,伤了,残了……都是钱巍担心的内容之一。
“监狱跑得怎样?”打通了电话,钱巍第一句话就问监狱。
“还没有跑得呢。”
“什么呢?去了两天了还没跑?”虽然没说出来,但钱巍感觉到一定出了事,还是大事,苟洱的语气平静得就像一场蓄攒了多日的倾盆暴雨。钱巍知道,如果这场大雨下来了,那就是排山倒海之势,“那你还好吗?”
好在苟洱把这股势力压住了,“我还没死。”苟洱说话坚硬,没有一点弹性,她一贯如此了,让人听了就想挂掉电话。
“乖乖,我知道的。你没事就好,我一直担心你的安全。”钱巍耐心非常好。
苟洱听到这句话就忍不住了,她放死地大哭,她不管电话那头钱巍的耳膜是不是被她震破了,反正她要哭,像个孩子。这种哭法是钱巍不曾想到的,在钱巍眼里,她是一个独立而骄傲的警花,插在瓶子也能活,而且还娇鲜庞艳,即使成了干花,也拥有世上最优美的身形,她不仅值得爱慕,还值得敬重,她的存在,让人觉得每走近一步,每靠近她一点,都是一种亵渎。
苟洱告诉了他所有的事实。
“这些,我估计过是个开始,顶多是个插曲。你还不知道呢,这个案子,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刘驼子的两个儿子,大的越狱了,小的不知道在哪,我估计他不会闲着。”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乖乖了?……难听死了,告诉你,我现在想杀人,求你别惹毛我。”
“那么大的火干吗?不利于排卵哦,小心输卵管堵塞,今后不能为我生孩子。”钱巍调侃道,他想缓解一下苟洱狂躁的情绪。
“去你妈的!”苟洱差点想骂“我*那个什么你妈”了。这种时候开这样的玩笑,苟洱没法接受。
钱巍非但不气,还安慰道:“你已经是刘胡兰了!”
“你可以说句人话吗?”
“那当江姐吧!”
“我挂了!”
“别,正经事还没说呢?”
“你没说还是我没说?什么情况你不都知道了吗?”苟洱道。
“需要我帮你分析案情吗?”
“那就免了,我最讨厌像你这样没名片的诸葛亮了。”苟洱喘了口气,接着说,“你猜,我看见谁了?”
“你怎么跟我学?卖关子了呢?你告诉你们头了吗?”钱巍有点紧张了。
“没,他没工夫听,他只想听结果,比如人死了和还是活了。”
“那你看见什么了?不会是看见男人在喷泉裸体洗澡吧?”
“钱巍,当初我头都不回离开你,还真是对的。我真挂了!”
“我听,听你的不行吗?刚我把耳朵掏干净了,一点粪都留下,算是有诚意吧?”
“那我告诉你啊,在听证会上军用机械厂计生办主任龚小婷讲的那个贵州女人,像神经病了那个,我上次找技术室的三维画像来着,觉得挺像,我刚在广场上看到她了,应该是她,我拍了照片,回去后请他们认一下。如果确定是他,这个地方就要密切关注了,它是我办案的突破口。”
说完苟洱就后悔了,什么时候起自己把钱巍当成自己的成长日记?
“你确定?”
“不确定,但我直觉告诉自己就是。”
“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但还是要进一步证实。告诉你一件事。”
苟洱听着钱巍的话忽然很沉重,她以为钱巍又故作深沉开玩笑,反问道:“你怀孕了?”
钱巍没有笑,而是很低沉地说道:“谷妙儿的儿子已经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了。”
“他知道了么?”苟洱问。
“他”指的是谁,苟洱和钱巍心里都清楚,他们虽不是夫妻,可交往多时,俩人早有有了比夫妻还要夫妻的默契了。
“他回不来,还在那边,枪伤没好,下不来床。”
“他到底伤了哪里?严重不严重?”
“呃,这我就不清楚了,那边说下不了床,估计有点严重,不过,他枪伤没几天的,恢复也是需要时间,你说是吧?”钱巍又补充,“你去监狱查访时记得问一下那边探监的情况。这对你破案很重要。”
“我怎么觉得你像这案子的导演呢?”
“嘿嘿,要是我导演,肯定比现在这个幕后导演要导得好一百倍,不会留下这么多漏洞。”
“说真的,我快玩不下去了,我觉得自己筋疲力尽。”
“你的面前远远不止刘大娃这几个鸡零狗碎的人那么简单,你得把事情想复杂一些,否则……”
“否则什么?”
“我跟你们局长说不要再让你追查下去了,你搞不了的。”
“你凭什么去跟他们说不要我查下去?真是好笑。”
“我觉得,你还是早点回来。”钱巍把话筒当成苟洱,亲吻了三下。
麦古塘这所苗王监狱确实像钱巍说的,非常险峻,是易守难攻的地形,逃一个人只要一天的功夫,追捕起来起码要一年。
这个监狱当初是苗族土司王建的秘密监狱,把那些对头秘密关在里面,通过折磨他们来打倒政治势力,所以,这土监狱是贵州土皇帝的御用监狱,相当于苗王的大理寺。
此监狱的墙是由各种巨石斧砸碎碾后的形状大小一般大的石头砌成,高虽然高,可是并不难攀爬,身手稍微好一点的都可以攀爬上去,但这个监狱的中间有一个岗亭,24小时不离人,这是建国改造后的,以前没有这个,土皇帝在最高的石墙顶端的石缝里都埋有炸药,谁爬上去,只要动一动就会炸到山下去,不死才怪,苗王时代,越狱的没有一个是活着出去的,那是土皇帝最得意的发明创造。后来被政府收了,装上了监狱标配,比如探照灯和电网,所以疑犯轻易不敢爬上来,但前几天,电网突然没电,刘大娃才得以翻出去的。
可警车还没开到一半就上不去了,底盘还不够高,而且火花塞废了,苟洱和另一个警官被困在半路,呆了半天,两人只好徒步而上。
边走苟洱边想,这么陡峭的地方,刘大娃他可以啊!随随便便就越狱了,倒回去70年,在二战中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盟军俘虏还是因为詹姆斯为期一年的策划才能成功逃狱,如果不是几百号战俘挖地道,詹姆斯组织再周密有何用呢?
随同小王警官见苟洱有些喘粗气,还东张西望的,便关切地问:“还吃得消吧?东张西望的,想什么呢?这山,就是我们本地人,也要体力好,还要熟路,要不也是难攀上去的。”
苟洱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半夜三更和一个毫不熟悉的同事小王翻山越岭。她稍微歇了口气,问道:“你们这苗王监狱不算榜上有名的监狱呀!人家弗州里士满利比监狱(美国),条件太差劲了,又有一个上校和一个少校领队,打通地下室的烟囱和挖隧道,最厉害的是他们搞了发明创造,他们可是行伍出身的呀,懂电气,懂技术。这苗王监狱的人,你说,那刘大娃,他懂什么?”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也不是所有越狱的人都一定要懂技术,恶魔岛(美国)上的犯人就靠一米宽的水电管线逃跑了出去的,你猜?他们用什么挖墙,混凝土墙啊?用勺子,指甲刀,钱(硬币),他们把吸尘器的马达做成了一个电钻,挖出了一个比狗洞大一点的洞逃出去了呢。也许是人求生的本能激发了人的潜能吧,我想,这个命题是可以好好研究研究的。”
苟洱没想出来一个出来做刑警的人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好研究研究,做学问那是坐办公室的人的事,她可不想越趄代庖。
从苗王监狱的结构聊到白天中央广场的枪战,小王知道的情况很少,他从来没有一个人面对过这么复杂的场面,他对苟洱的应便很崇拜,他觉得苟洱更应该留下来去善后,而不是大半夜的去什么苗王监狱。苟洱背了任务,也不便多说,毕竟跨了省,而且有的事必须保密。
两人实在走不动了,便在小径上的泥土地上盘腿而坐。
四周静谧无比。
小王找了个新话题:“我脑袋里神经元,哦,二级神经元活动的声音我都可以听得到。”
苟洱笑了笑,附和着说:“哦,那我可以听得到你血管里血流的声音了。”
“五官过于敏感也不是什么好事。”
“哦,你怎么这么感慨呢?”
“苟警官,你不知道,就在我们坐的这里,总有狗跳崖自杀。”
“啊!不会吧?怎么会有狗跳崖自杀?狗也有自杀的吗?”
“当然了,你不要以为只有警犬战役犬郁郁寡欢而自杀,普通狗也会自杀的。”
“那我可没听说过。你说说看!”苟洱兴趣来了。
“这里自杀的狗都是猎狗,他们嗅觉太灵敏了,比一般的看家土狗要厉害。但就是因为太厉害才死的。只要上山来踩药的人或猎人带着狗上山,到了这,一不留神,狗就跳崖了。已经有18只猎狗自杀。我们这的本地人信巫术,说是神在保佑苗王留下来的那座监狱,一般人都不会上来,不敢上,怕神咒,其实,一般也就采药人和猎人上来,到了我们这个位置,就不会上走了。你看,那上面的路,你不仔细分辨还真看不出来呢。”
“不可能是神主宰吧?”
“那是,我不是有神论者,但我也不会在本地人面前说这个,那是大忌讳,你的工作没法开展下去的。外省的专家拉了些洋专家来我们这,有搞地质的,也有生化家,他们发现下面简直就是一个动物大墓场,上了电视和报纸的,他们找到的动物的残骸就有200多种,不知道它们都是怎么集中死亡在这下面的,把残骸带回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做化验,发现是这里的一种黑色的岩壁蛇释放了一种叫什么ND什么的物质,比较香,有引诱和麻醉的作用。但地质家说,是这里的瓜洼喀斯特的岩石结构,有太强的空气对流作用,尤其是秋季和冬季,下午一点到四点之间,闻到这种气体的动物会眩晕,产生幻觉,然后被强对流空气给吸了下去,看起来就像跳崖自杀了。”
“这样的呀!”苟洱惊得合不上嘴,她屁股赶紧挪动了。
苟洱的受刺激让小王警官乐得直笑:“不会马上就有岩壁蛇上来的,这个季节,很安全,再说,你我又不是狗,岩壁蛇也是看菜下饭的。”
不管小王怎么说,苟洱是坐不住了,她听得头皮都发麻,赶紧跳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小王也起身了,苟洱回头看看这寂静了千百年的大山,不知发生了多少血雨腥风的大事,苟洱倍觉惋伤凄凉,自己呢?自己还会有后代吗?像大山那样,在默默寂静的岁月中繁衍生息,即使遇到了灾难也能自夺生路。苟洱又想起未来的某一天,假如自己突然死去,谁会知道自己死去或曾经活着?
怪兽和小虫时不时地对语一声,表示着一切沉默物的存在。大山总是默默地,从不回答,它只冷眼看着世间所有的冷暖。
苟洱用她带着远视的肉眼看清了山的地形,羊肠小道若隐若现,小王说得对,只是不知道通往哪。
不知不觉就过了凌晨一点,苟洱他们赶到了监狱,可监狱长却回家了。接待他们俩的是值班监狱长,他说监狱长之前电了苟洱和她同事,没有手机信号,监狱长以为他们不会来了,所以晚上并没有在监狱等他们。
苟洱调出了刘大娃入狱后的所有资料。一共有三个人来探过监,分别是刘细娃、刘生铁(刘驼子)、孔相。
刘细娃来过五次,分别是五月一次,六月两次,然后是今年的八月两次。
刘生铁只来过一次,是今年的三月。
孔相在刘大娃越狱前的两个月里来过两次。
因为监狱长不在,值班狱警没有权限打开身份证核实系统,苟洱把孔相的资料传给罗坪所,罗坪所回复说身份证是假的,苟洱惊问:“怎么可能是假的?入狱时都是要核对资料的,没有证件怎么入狱?”但值班狱警耸耸肩。
苟洱又把三只手余谈的相片拿给狱警看,他说没见过,时间那么久了,记不得,但他又提醒,如果让当班的狱警辨认也许他们有印象,毕竟来探监的人并不多。
当班狱警就在营房睡着,他半夜被叫起来辨认,他一眼就认出,那个“孔相”就是三只手,余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