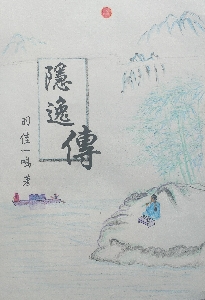对于苟洱出生入死的办案,局里半句表扬的话都没有。相反,局里召开了两次批斗会,批了就算了,还要写检讨。
苟洱读书那会儿,最不会写的就是检讨,其次是情书,但凡她要会写煽情的情书,后来的苟洱也不至于那么惨烈了。
苟洱成长过程中,从来没做过“错事”,最多就是在同学回答问题时她把同桌的凳子给抽了,让同学扑了空,所以她自不必写检讨了。她收获最多的,是表扬。老师和父亲的表扬。从她记事起,爷爷就像一盏常明灯,一直照亮着苟洱。
也正因为受这种统教育多了,苟洱的情感世界滞后得近乎空白。如果说苟洱完全没有情感生活也说不过去,毕竟她也收到过三封无字天书。
但苟洱情商发育低下,她死活也搞不明白,来信不是信封上没有署名就是信里没有任何字,哪怕蚂蚁的尸体都行啊!可信纸里什么都没有。
苟洱在日记里写道:既然写信,为什么不写一个字?既然不愿意说一个字,干吗又花七分钱以上的邮票费?莫非是特务接头的信号?那时,特务的余热还残留着。苟洱乐此不彼。
她为此找到父亲,要他一定要弄到了显影水,父亲当着她的面把信显影出来了,可还是什么都没有。于是,父亲就用异样的眼睛看着苟洱,还用他那宽厚的巴掌抚摩苟洱的马尾巴,憨憨地笑着。
如今,苟洱因放跑嫌犯,让4名无辜群众误死被局里关了起来,她必须写检讨,别说枪了,连通信工具都被没收了。对她来说,在禁闭室写检讨无疑是一场文学考试。在网上找范文和找钱巍代笔都不成。她甚至设想了一场交易,如果钱巍现在愿意帮她写检讨,她宁愿闭上眼睛让钱巍亲吻一次。
检讨没捣鼓出来,贵州那边就来人了,中央广场死者家属闹得不可开交,要赔偿,最低是五十万,老太太的儿子张嘴就是两百万。罗坪所没招了,只好让苟洱这边来收拾。
苟洱的黑锅,背定了。
她想找局长谈,可局长根本不见她。她又找易副所长,他正被那群人追得满地跑,焦头烂额,分身乏术。
禁闭关到第三天的时候,是钱巍救了她。钱巍帮她出了十万块钱,局里给死者家属每人给了十万丧葬费,罗坪那边负责本地的安葬费,这事才算了了。
从禁闭室出来的那天,蒋局长正好把记者赶走,检察院的人又来找蒋局长,他指着苟洱的鼻子,用他那僵硬的手指头朝苟洱狠狠地点了点,气鼓鼓地走了。
苟洱从来没有这么觉得难受,当时眼泪就掉了下来。正好钱巍在身边,她扭过头就伏在钱巍的肩膀上大哭起来,过往的同事看着她,什么都不说,笑了笑,自顾自干活去了。
苟洱歇斯底里地海哭了一通。
哭累了,她便从钱巍肩头离开,他肩上衣服+湿了一大块,是口水还是眼泪或者鼻涕糨糊已经搞不清了,钱巍正准备带苟洱离开,易副局长过来了,他把苟洱喊到谈话室。
易副局长这次很快地开门见山了:“局里准备停你三个月职。你有什么意见?”
“什么?停职?为什么?”苟洱的反问有点儿韩剧里毫无新意的台词。
“我真的爱莫能助。”
苟洱眼睛瞟到墙上,日光灯照白的地方,一只飞蛾子正在忙不迭地往镇流器上扑。“你们既然都已经决定停职了,还问我有什么意见?”
“那从今天开始了,你回去休息三个月吧。也许那时候,案子应该,应该已经破了。”
苟洱觉得自己像一块抹布一样,被人丢在垃圾筒里。她什么也不想解释,她只想哭,没了枪,眼泪成了她的第一武器。至于这个武器可以对付谁,苟洱管不了那么多,刚刚在钱巍那里没哭够,她还要哭,谁让自己是个女人?以前故作坚强,可自己到底是个女人,是女人,就得哭,不哭还是什么女人?
直到办完了交枪手续,苟洱才忍住了哭,她原本想一直憋到办完手续才哭的。没了枪,等于自己丢了警察的身份,丢掉了一份可以为民除害的资格,这比打死苟洱还要让她觉得屈辱。
钱巍已经在车里等她了,见到他,苟洱又是一阵梨花飘零似的倾泻,她一反往日的高傲、矜持、肃静,她趴在钱巍的右肩上,又是拍又是打,叫声吠乱。顿时,这些乱七八糟的交响声和喇叭声掺合在一起,组成了一曲极其难听的交响乐。
因为钱巍的车堵住了后面来办事的人的车,后面的拼命按喇叭。钱巍不管,认真地看着苟洱哭,但此刻的他却丝毫都不敢抱苟洱,碰都不敢碰。他把两只手举在空中,像一个等着缴枪的俘虏。
“你抱我一下吧,你怎么不抱?你抱我呀?”苟洱骂道。
钱巍的手还举在空中。
“你是个死人呀?让你抱都不抱?你不是想抱我吗?”苟洱越来越气了,她干脆半躺在钱巍身上,一手抓起车钥匙启动起车来,吓得钱巍赶紧放下了手,摸了摸她凌乱的头发:“我们回家。”
还没等苟洱问“回家”是什么意思,后面办事的人出了门,上来骂街了。
当他插了腰站在钱巍面前时,苟洱和那男人彼此都认出了是谁,那人原来是给苟洱治疗蜈蚣毒的医生。
他见钱巍手里搂着苟洱,本想说点什么,但他还是犹豫了,钻进车里去了。
钱巍把手轻轻放下,头伸出去,问男人:“付医生,你怎么在这里?”
那个叫付医生惊奇地问:“你是……?”
“我是谷妙儿的好朋友,你到公安局来做什么?”钱巍答。
苟洱也惊奇不已,听口气,付医生并不认识钱巍,但钱巍却认得付医生!
“哦,你是谷医生的朋友呀!她没告诉你么?她的儿子……没了……”付医生慢慢地说,他的语速和事情的过程和“死”配合得相当和谐。
“什么?”
钱巍和苟洱几乎异口同声。
“你再讲一遍!你再讲一遍!!”钱巍推开苟洱,下了车,立即朝付医生的车冲了过去,苟洱怕钱魏干架,抹了抹眼泪,也下了车。
付医生顿了顿,说:“今天早上的事了,8点03分去的。我是来你们这帮谷医生办销户手续的,这不,还差一道死亡鉴定,她自己不能开证明,得找其他医生,又补了一个。”付医生掏出销户回执来。
“你再讲一遍!你再讲一遍!!”钱巍失控了,苟洱很害怕,她没见过钱巍那么冲动,从没有。
“她儿子没了。”钱巍喃喃自语,他不断地重复这句空洞的话。
“我昨晚还去看了她儿子,还吊着气呢,怎么就没了?”钱巍声音忽然又高亢起来。
付医生一本正经地说:“谁跟你开玩笑,这种事。”
“我现在就去。”钱巍说,“我现在就去,要是他没死,我,我回来揍死你!”
“拜托,你把车拐过去一点吧。我怎么进去呀!”付医生在车里喊道。
钱巍什么也不再说了,朝车里钻了进去,苟洱愣在那。
“你去还是不去?”钱巍的眼睛瞪得和个豹子头林冲一样,苟洱慌忙钻进了车里。
一路上,两人都沉默。钱巍的车开得很快,一连闯了三个红灯,至少要交600块钱罚款。
苟洱小心翼翼地问:“谷妙儿的儿子有十几岁了?”
“十岁零一个月三天。”钱巍答道。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苟洱很惊讶,但又有些不舒服,钱巍记得自己的生日,怎么对那小孩子的生日也记得那么清楚?
“当然,要是你是我,也记得那么清楚。”
苟洱没经历过男女之事,她忿然道:“我又不是你,怎么可能那么清楚。”
“闭嘴!”
苟洱看到钱巍第一次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发火,她也莫名其妙地火上心来:“下车。”
钱巍:“你说什么?”
“下车!”
“谁下车?”
“我。”苟洱用鼻子哼了一句。
“你干嘛?”
“不干嘛。”
钱巍忽然把方向盘一右拐,车朝着人行道上开了去,他又突然把车打急刹了,苟洱被震了一下,头朝前一倾。她正要骂人,钱巍已经从车里出来了,绕道苟洱这边,迅速把她从车里拖了出来,死死地抓住她的肩膀,抱住苟洱的头就拼命地乱吻,舌头要进到苟洱的喉咙里去了,她被窒息得要死的感觉。好不容易挣脱了,她真想立即抽钱巍一耳光,可她的手,像断了筋一样,没举得起来。
钱巍猛地把苟洱一推,绕到车里,却两眼发怔,呆呆地说着:“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回到屋,苟洱像从魔鬼海游了一圈回来,这一天来发生的事简直就是恍如前世的感觉。
疯了一般的钱巍说出来的话就像墓地里放鞭炮,吓死人。
“当初你写的那信是真的?你们一直情深意重?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她?”苟洱没法忘记那封信,信的威力堪比“沙皇炸弹”的RDS-220氢弹威力!因为罗佰义无情无义,苟洱真不打算结婚的,但父母不答应,她又不想违逆,所以想着,就这么着算了,没爱情就没爱情,婚姻是女人的一个坎,迈了过去就迈了,好呀坏呀无所谓,既然不能和心爱的人过一辈子,找个爱自己的也成。
回想起钱魏的那封信,确实比“沙皇炸弹”还让苟洱恐慌。“沙皇炸弹”遥不可及,可钱魏的事却没那么简单,而且,演绎不断。白莲为罗佰义跳楼,遗书都没写得那么情深款款,如果白莲当初遇到的是钱巍,不是罗佰义,那么,白莲就不会死了,苟洱对自己说。
苟洱想起车里,钱魏的话来,“说来话长……我只能告诉你,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我们把最真诚的感情都给了对方。”
“包括肉体?”苟洱抿嘴笑问。
钱巍严肃地说:“她比我还痛苦,我不知道那时她已经有了我孩子。”
“什么?还怀了你的孩子?听起来,你们像在演电影!?”苟洱惊叫并嘲讽着。
“随你怎么说。”
“那你怎么还抛弃她?”
“我们谁也没抛弃谁。”
“你没抛弃她?又怎么那么急不可耐地和我结婚?而且,你,你那你刚才还……”苟洱把手指头压在自己嘴唇上。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能抱她,我……”钱巍一脸平静,可苟洱看到他平静的后面并不是一潭死水,是什么?苟洱说不上来。
钱巍眉头紧锁,眼睛看着前方,那分明是一个空洞的前方,“我难受。我不想解释什么。原谅我,我只能这么说。对不起,刚才是我,该死。我冒犯了你。”
钱巍词不达意的结巴着,不像平时说话,太不利索了。苟洱这才知道,原来他把自己当成谷妙儿了。这到底是谷妙儿的幸运还是自己的不幸?苟洱搞不懂。钱巍空洞的目光又扫向近处的玻璃大楼,苟洱从钱巍眼球里来回映射的光芒中捕捉到他在光怪陆离的玻璃光之间的挣扎和游离。末了,他告别了短暂的失控,踩着油门,猛打方向盘,朝着红灯开去。
苟洱能感受到钱巍的心盛满了一桶汽油,一点就着。
夜已经深透了,心烦意乱的苟洱,此时此刻,只想安静。她只能安静,安静,再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