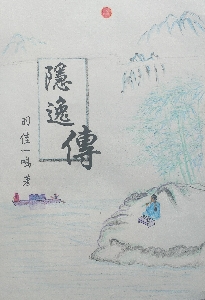鹤连空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踏下清天观的最后一个台阶的。伤口早已不再流血,衣襟已被血液染得暗沉,粘稠的血液凝固成硬块紧贴着他的伤口和衣襟,将衣物与皮肤黏连在一起。每一步的移动,都像是撕扯开那层血痂,锥心刺骨的疼痛以让他几近麻木。
他站在原地,四处环顾。这里的气候温和宜人,天空湛蓝如洗,阳光柔和地洒在大地上。西边望去,群山连绵起伏,还有几处村庄。山脚下蜿蜒着清澈的河流,水波潺潺。再往东边望去,隐约可以看到一片辽阔的海洋,海风带着些许咸味,湿润的气息拂过鹤连空的脸庞。
他笑了,“真美。”
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他踉踉跄跄地向着一个小木屋的方向走去。木屋的轮廓渐渐清晰,几缕炊烟带来些许人间的温暖。他几乎是拖着身子走向门口,他虚弱地抬手,轻轻敲了敲门,那声音微弱得几乎被夜风吹散。
木门缓缓打开,透出一丝昏黄的灯光,照在他苍白的脸庞上。鹤连空再也撑不住了,他的身体一软,顺着门框滑落,意识在昏暗中逐渐消散。耳边仿佛传来了一声急促的呼喊,但他的眼前已经一片漆黑。
又不知过了多久,鹤连空在一片朦胧中渐渐苏醒,他嗅了嗅,周围的空气清新而湿润,耳边还传来风拂过草地的轻响。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天空蓝得深邃,几缕白云悠闲地漂浮着。
他微微动了动身体,感到全身的疼痛比之前稍稍减轻。低头一看,自己身着一身干净的衣裳,身上的伤口已用布条简单地包扎好。身旁放着几瓶药草,几片干粮,一个小布袋子。
他缓慢坐起身,草地安静而平和,远处可以看到几棵高大的树木,树影婆娑。鹤连空将一只手轻轻放在胸前,感受着自己心脏有力的跳动,虔诚地说道:“谢谢。”
鹤连空打开布袋,里面放着约莫二三十粒八角形的银粒。鹤连空拿出几粒细看,每一粒都有一个面上雕刻着一颗大树,棱角则刻波浪纹样。拿在手中具有独特的分量感,光滑而不失厚重。“银钱?”鹤连空想。
鹤连空来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四处走着。
他见期刊登了一首关于自己的诗,听说最后一句还是那位举世闻名的苍洲小王姬所作。
“清天观,清风君,一夕倾,一朝陨。
未成性,天妒英,九成尽,君成禁。
风轻吟,志未平,名犹青,泪满盈。”
他微微笑着,在温暖的阳光下,想起昔日一段对话。
一次师弟问他:“如果有一日你真的失去了一切,还能面不改色的说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吗?”
当时他的回答是:“万物皆因缘而起,因缘而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皆是暂时的借用。失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心中的执着。我会深入观察自己的内心,看到痛苦的根源,正是我的执着。看破这些执着,便能放下。真正的财富,是内心的平静、智慧、慈悲。”
他轻抚破碎的九天苍龙。
“吃了二十年的斋饭,让老子且去放纵一回再说。”他潇洒地说道。
日暮时分,鹤连空来到村庄中一处小馆。馆内的装饰简单而温馨,几张木质桌椅摆放在窗边。
“客官里面请。”店里的小二见客人进门,立刻迎了上来,挂着殷勤的笑容,声音热情而干练。小二领着鹤连空到一个角落的位置,待他坐下,小二热情道:“来点什么?”他随手翻开桌上的菜谱,目光在上面扫了一眼,随后用手指了指几道两三灵银,价格较低的菜,道:“这些吧。”“好嘞,马上。”
就在他专注于眼前的美食时,邻桌的谈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位中年男子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焦虑和不安道:“你看今日的期刊了吗?听说漠北要和苍洲联盟了。”
对面的那位语气中满是鄙夷:“漠北?那地方简直是蛮夷之地,荒凉偏远,民风彪悍。王室怎么说?”
中年男子耸了耸肩,无奈地叹了口气:“王室的态度还不明朗,事情还没有准信。不过,王室期刊也不是空穴来风,恐怕我们都要小心为上。”
鹤连空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心中暗自思索。
这消息若属实,苍洲和漠北的联盟将会在大陆上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漠北勇猛的战斗力和强大的骑兵部队从未被人小觑,而苍洲一向以其经济发达而闻名,若两者联手,将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引起他国警惕。可是以漠北的行事作风,事情应该并不是只有联盟这么简单。这片土地上,风起云涌,暗流涌动,似乎有一场更大的变局正在酝酿。
清天观隐秘于山中,教导着法术和学术。弟子们被选为神使方可下山,或各处传教或处理国家事务,而像鹤连空这般私自下山的便会遭受神罚。鹤连空在清天观的时光除了修炼,还花费了大量时间钻研奥亚大陆的各个国家,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与鬼先生一起,他还特别研习了联盟连横。
听二人的对话,他判断自己现在应该是身处苍洲境内。或许可以先去一趟姑苏,探究其中所以然。他收回思绪,低头继续吃饭,“不去。”
“我又不是顾清风,我管那事作甚。”
吃过晚饭后,鹤连空漫无目的地在村子的石板路上踱步。他见不远处有一棵老槐树,觉得顺眼,便慢慢走过去,靠在树干上。他伸手从怀里摸出一把瓜子,随意地嗑着。仰起头,半眯着眼看向天边的夕阳,懒洋洋地吐出一片片瓜子壳,在地上堆积成一小堆。他的模样邋遢不堪,蓬乱的头发和满脸的灰尘让他看起来像是个游荡已久的乞丐,裸露的双手和脖颈上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疤痕。
他没有到清天观之前的丁点记忆,仿佛从出生起就在清天观一般。除了顾清风之外,他已经忘了如何做鹤连空。“何去何从呢?”他轻声自问。
他把最后一颗瓜子放进嘴里,吐出壳子,然后随手在地上捡起一根细长的树枝,在地上画着圈子,像是无聊的小孩。
树枝在地上划过的声音与夕阳西下时的微风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的宁静。
他低头看着自己满是疤痕的双手,嘴角微微扬起,带着一丝自嘲。顾清风早已成为过去,他不用再去思考荣耀与失败。曾几何时,他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不再是圣光教呼风唤雨的顾清风,而是奥亚大陆的鹤连空,一个没有定义的人。
鹤连空靠在树干上,瓜子壳散落在地,夕阳的余晖逐渐减弱,天空中的橙红色慢慢被深蓝取代。“也许……没有归宿也是一种归宿吧。”
夕阳的最后一丝光芒消失,夜幕即将完全降临。
鹤连空在那棵树下靠着,不知不觉中便闭上了眼睛。
第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树叶,洒在他的脸上时,鹤连空慢慢醒了过来。他睁开眼,感受到温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眼前的一切仿佛蒙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他眨了眨眼睛,半梦半醒之间,有些迷茫地看着周围的景象。
过了片刻,他才完全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仍旧在一个村庄里,身边依然是那棵昨晚他倚靠的老槐树。
村庄已开始苏醒,远处传来几声鸡鸣,村民们也陆续走出屋子,开始一天的劳作。
风轻轻吹过,带来了一丝凉意。鹤连空收回了目光,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满是尘土的靴子,脚下的路似乎无尽延展,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走吧,天亮了。”他对自己说道。